陳紫微赴召 其二
苦心如檗凜于冰,贏得沖冠雪一簪。千載四明登陸處,三生五月度瀘心。清泠烈暑生秋思,諧協涼薰入正音。今日憚公如憚黯,試看塞柝夜沈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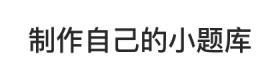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苦心如檗凜于冰,贏得沖冠雪一簪。千載四明登陸處,三生五月度瀘心。清泠烈暑生秋思,諧協涼薰入正音。今日憚公如憚黯,試看塞柝夜沈沈。
洞庭為沅湘等九水之委,當其涸時,如匹練耳;及春夏間,九水發而后有湖。然九水發,巴江之水亦發,九水方奔騰皓淼,以趨潯陽;而巴江之水,卷雪轟雷,自天上來。竭此水方張之勢,不足以當巴江旁溢之波。九水始若屏息斂衽,而不敢與之爭。九水愈退,巴江愈進,向來之坎竇,隘不能受,始漫衍為青草,為赤沙,為云夢,澄鮮宇宙,搖蕩乾坤者八九百里。而岳陽樓峙于江湖交會之間,朝朝暮暮,以窮其吞吐之變態,此其所以奇也。樓之前,為君山,如一雀尾壚,排當水面,林木可數。蓋從君山酒香、朗吟亭上望,洞庭得水最多,故直以千里一壑,粘天沃日為奇。此樓得水稍詘,前見北岸,政須君山妖蒨,以文其陋。況江湖于此會,而無一山以屯蓄之,莽莽洪流,亦復何致。故樓之觀,得水而壯,得山而妍也。
游之日,風日清和,湖平于熨,時有小舫往來,如蠅頭細字,著鵝溪練上。取酒共酌,意致閑淡,亭午風漸勁,湖水汩汩有聲。千帆結陣而來,亦甚雄快。日暮,炮車云生,猛風大起,湖浪奔騰,雪山洶涌,震撼城郭。予始四望慘淡,投箸而起,愀然以悲,泫然不能自已也。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,郁郁不得志,增城樓為岳陽樓。既成,賓僚請大合樂落之,子京曰:“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!”范公“先憂后樂”之語,蓋亦有為而發。夫定州之役,子京增堞籍兵,慰死犒生,邊垂以安,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后。朝廷用人如此,誠不能無慨于心。第以束發登朝,入為名諫議,出為名將帥,已稍稍展布其才;而又有范公為知已,不久報政最矣,有何可哭?至若予者,為毛錐子所窘,一往四十余年,不得備國家一亭一障之用。玄鬢已皤,壯心日灰。近來又遭知己骨肉之變,寒雁一影,飄零天末,是則真可哭也,真可哭也!
夜雪大作。時欲登舟至沙市,竟為雨雪所阻。然萬竹中雪子敲戛,錚錚有聲,暗窗紅火,任意看數卷書,亦復有少趣。
自嘆每有欲往,輒復不遂。然流行坎止,任之而已。魯直所謂“無處不可寄一夢”也。
天霽。晨起登舟,入沙市。午間,黑云滿江,斜風細雨大作。予推篷四顧:天然一幅煙江幛子!
乙未,中郎令吳,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隱,散于四方,乃取子瞻懷子由之意,扁其退居之堂曰“聽雨”。十月,予往吳省之,見而嘆曰:“吾觀子瞻居宦途四十余年,即顛沛流離之際,室家妻子瀟然不在念,而獨不能一刻忘情于子由,夜床風雨之感無日無之,乃竟不得與子由相聚也。”
嗟乎!宋自仁宗以后,皆非治朝也。子瞻之骯臟好盡,子由之狷介寡合,皆山林之骨,非希世取功名之人也。古之君子,有一人知之,則可以隱。夫孰有子瞻與子由兩相知者?以兩相知之兄弟,而偕隱于山林,講究性命之理,彈琴樂道,而著書瑞草、何村之間,恐亦不大寂寞也;而乃違性乖質,以戰于功名之途,卒為世所忌,幾至于死。彼黃州之行已矣,元祜初,既得放歸陽羨,當此時,富貴功名之味,亦既嘗之矣;世路風波之苦,亦既歷之矣;己之為人,足以招尤而取忌,亦大可見矣,肱已九折矣。或招子由至常,或移家至許,或相攜而歸,使不得遂其樂于中年者,庶幾得遂于晚歲,亦奚不可。胡為乎招即來,麾即去,八年榮華,所得幾何?而飄零桄榔之下,寂寞蜒島之中,瀕海相逢,遂不得與子由再見,此吾之所不曉于子瞻者也。夫人責自照。陶潛之可仕而不物,以其性剛耳。子瞻渡海以后,乃欲學陶,夫不學之于少,而學之于老,是賊去而彎弓也。
今吾兄弟三人,相愛不啻子瞻之于子由。子瞻無兄,子由無弟,其樂尚減于吾輩。然吾命薄,或可以免于功名。獨吾觀兩兄道根深,世緣淺,終亦非功名之品。而中郎內寬而外激,心和而跡孤,尤與山林相宜。今來令吳中,令簡政清,了不見其繁,而其中常若有不自得之意。豈有鑒于子瞻之覆轍,彼所欲老而學之者,中郎欲少而學之乎?如是則聽雨之樂,不待老而可遂也,請歸以俟。
金粟園后,有蓮池二十余畝,臨水有園,楮樹叢生焉。予欲置一亭納涼,或勸予:“此不材木也,宜伐之,而種松柏。”予曰:“松柏成陰最遲,予安能待。”或曰:“種桃李。”予曰:“桃李成蔭,亦須四五年,道人之跡如游云。安可枳之一處?予期目前可作庇陰者耳。楮雖不材,不同商丘之木,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,蓋亦界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。以為材,則不中梁棟枅櫨之用;以為不材,則皮可為紙,子可為藥,可以染繪,可以颒面,其用亦甚夥。昔子瞻作《宥老楮詩》,蓋亦有取于此。”
今年夏,酷暑,前堂如炙,至此地則水風泠泠襲人,而楮葉皆如掌大,其陰甚濃,遮樾一臺。植竹為亭,蓋以箬,即曦色不至,并可避雨。日西,驕陽隱蔽層林,啼鳥沸葉中,沉沉有若深山。數日以來,此樹遂如飲食衣服,不可暫廢,深有當于予心。自念設有他樹,猶當改植此,而況已森森如是,豈惟宥之哉?且將九錫之矣,遂取之以名吾亭。
功德寺循河而行,至玉泉山麓,臨水有亭。山根中時出清泉,激噴巉石中,悄然如語。至裂帛泉,水仰射,沸冰結雪,匯於池中。見石子鱗鱗,朱碧磊珂,如金沙布地,七寶妝施。蕩漾不停,閃爍晃耀。注於河,河水深碧泓,澄激迅疾,潛鱗了然,荇發可數。兩岸垂柳,帶拂清波,石梁如雪,雁齒相次。間以獨木為橋,跨之濯足,沁涼入骨。折而南,為華嚴寺。有洞可容千人,有石床可坐。又有大士洞,石理詰曲。突兀奮怒,皺云駁霧,較華嚴洞更覺險怪。后有竇,深不可測。其上為望湖亭,見西湖,明如半月,又如積雪未消。柳堤一帶,不知里數,裊裊濯濯,封天蔽日。而溪壑間民方田作,大田浩浩,小田晶晶,鳥聲百囀,雜華在樹,宛若江南三月時矣。
循溪行,至山將窮處,有庵。高柳覆門,流水清澈。跨水有亭,修飭而無俗氣。山余出石,肌理深碧。不數步,見水源,即御河發源處也。水從此隱矣。
明日過桃源縣,之綠蘿山下諸峰累累,極為瘦削。至白馬雪濤處,上有怪石,登舟皆踞坐。泊水溪,與諸人步入桃花源,至桃花洞口。桃可千余樹,夾道如錦幄,花蕊藉地寸余,流泉汩汩。溯源而上,屢陟彌高,石為泉嚙,皆若靈壁。
水聲咽,中夜蘭橈暗發。殘春在,催暖送晴,九十韶光去偏急。垂楊手漫折,難結,輕帆一葉。離亭遠,歸路漸迷,千里滄波楚天闊。
除寒乍消歇。剩霧鎖花魂,風砭詩骨。茫茫江草連云濕。悵綠樹鶯老,碧欄蜂瘦,空留檣燕似訴別,向人共愁絕。 重疊,浪堆雪。坐縹緲浮槎,煙外飛越。銜山一寸眉彎月,照枉渚疑鏡,亂峰如發。扁舟獨自,記舊夢,忍細說?
登臨縱目,對川原繡錯,如襟接袖。指點十三陵樹影,天壽低迷如阜。一霎滄桑,四山風雨,王氣消沈久。濤生金粟,老松疑作龍吼。 惟有沙草微茫,白狼終古,滾滾邊墻走。野老也知人世換,尚說山靈呵守。平楚蒼涼,亂云合沓,欲酹無多酒。出山回望,夕陽猶戀高岫。
斜月半朧明,揀雨晴時淚未晴。 倦倚香篝溫別語,愁聽,鸚鵡催人說四更。 此恨拚今生,紅豆無根種不成。 數遍屏山多少路,青青,一片煙蕪是去程。
百五韶光雨雪頻,輕煙惆悵漢宮春。祇應憔悴西窗底,消受觀書老去身。
花影暗,淚痕新,郢書燕說向誰陳。不知馀蠟堆多少,孤注曾無一擲人。
東別家山十六程,曉來和月到華清。 朝元閣下西風急,都入長楊作雨聲。
聞有南河信,傳聞殺畫師。 始知君念重,更肯惜蛾眉。
金溪民方仲永,世隸耕。仲永生五年,未嘗識書具,忽啼求之。父異焉,借旁近與之,即書詩四句,并自為其名。其詩以養父母、收族為意,傳一鄉秀才觀之。自是指物作詩立就,其文理皆有可觀者。邑人奇之,稍稍賓客其父,或以錢幣乞之。父利其然也,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,不使學。
余聞之也久。明道中,從先人還家,于舅家見之,十二三矣。令作詩,不能稱前時之聞。又七年,還自揚州,復到舅家問焉。曰:“泯然眾人矣。”
王子曰:仲永之通悟,受之天也。其受之天也,賢于材人遠矣。卒之為眾人,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。彼其受之天也,如此其賢也,不受之人,且為眾人;今夫不受之天,固眾人,又不受之人,得為眾人而已耶?
登臨送目,正故國晚秋,天氣初肅。千里澄江似練,翠峰如簇。歸帆去棹殘陽里,背西風,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,星河鷺起,畫圖難足。(歸帆 一作:征帆) 念往昔,繁華競逐。嘆門外樓頭,悲恨相續。千古憑高對此,謾嗟榮辱。六朝舊事隨流水,但寒煙衰草凝綠。至今商女,時時猶唱,后庭遺曲。(衰草 一作:芳草)
褒禪山亦謂之華山,唐浮圖慧褒始舍于其址,而卒葬之;以故其后名之曰“褒禪”。今所謂慧空禪院者,褒之廬冢也。距其院東五里,所謂華山洞者,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。距洞百余步,有碑仆道,其文漫滅,獨其為文猶可識曰“花山”。今言“華”如“華實”之“華”者,蓋音謬也。
其下平曠,有泉側出,而記游者甚眾,所謂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,有穴窈然,入之甚寒,問其深,則其好游者不能窮也,謂之后洞。余與四人擁火以入,入之愈深,其進愈難,而其見愈奇。有怠而欲出者,曰:“不出,火且盡。”遂與之俱出。蓋余所至,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,然視其左右,來而記之者已少。蓋其又深,則其至又加少矣。方是時,余之力尚足以入,火尚足以明也。既其出,則或咎其欲出者,而余亦悔其隨之,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。
于是余有嘆焉。古人之觀于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蟲魚、鳥獸,往往有得,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。夫夷以近,則游者眾;險以遠,則至者少。而世之奇偉、瑰怪,非常之觀,常在于險遠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有志矣,不隨以止也,然力不足者,亦不能至也。有志與力,而又不隨以怠,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,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,于人為可譏,而在己為有悔;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,可以無悔矣,其孰能譏之乎?此余之所得也!
余于仆碑,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,后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,何可勝道也哉!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
四人者:廬陵蕭君圭君玉,長樂王回深父,余弟安國平父、安上純父。
至和元年七月某日,臨川王某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