偈頌七十六首 其三十七
憶昔玉幾時,分贓不合火。今日驀相逢,依然眾恁么。不恁么,睦州擔板,云門腳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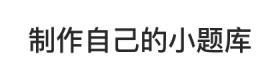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憶昔玉幾時,分贓不合火。今日驀相逢,依然眾恁么。不恁么,睦州擔板,云門腳跛。
雜虜橫戈倒載斜,依然南斗是中華。 金銀舊識秦淮氣,云漢新通博望槎。 黑水游魂啼草地,白山新鬼哭胡笳。 十年老眼重磨洗,坐看江豚蹴浪花。
板蕩凄涼忍再聞?煙巒如赭水如焚。 白沙堤下唐時草,鄂國墳邊宋代云。 樹上黃鸝今作友,枝頭杜宇昔為君。 昆明劫后鐘聲在,依戀湖山報夕曛。
瀲艷西湖水一方,吳根越角兩茫茫。 孤山鶴去花如雪,葛嶺鵑啼月似霜。 油壁輕車來北里,梨園小部奏西廂。 而今縱會空王法,知是前塵也斷腸。
方袍瀟灑角巾偏,才上紅樓又畫船。 修竹便娟調鶴地,春風蘊籍養花天。 蝶過柳苑迎丹粉,鶯坐桃堤侯管弦。 不是承平好時節,湖山容易著神仙。
冷泉凈寺可憐生,雨血風毛作隊行。 羅剎江邊人飼虎,女兒山下鬼啼鶯。 漏穿夕塔煙烽影,飄撇晨鐘鼓角聲。 夜雨滴殘舟淅瀝,不須噩夢也心驚。
建業余杭古帝丘,六朝南渡盡風流。 白公妓可如安石,蘇小湖應并莫愁。 戎馬南來皆故國,江山北望總神州。 行都宮闕荒煙里,禾黍從殘似石頭。
冬青樹老六陵秋,慟哭遺民總白頭。 南渡衣冠非故國,西湖煙水是清流。 早時朔漠翎彈怨,他日居庸宇喚休。 苦恨嬉春鐵崖叟,錦兜詩報百年愁。
閣于山與湖之間,山圍如屏,湖繞如帶,山與湖交相襲也。虞山,嶞山也。蜿蜒西屬,至是則如密如防,環拱而不忍去。西湖連延數里,繚如周墻。湖之為陂為寖 者,彌望如江流。山與湖之形,經斯地也,若胥變焉。閣屹起平田之中,無垣屋之蔽,無藩離之限,背負云氣,胸蕩煙水,陰陽晦明,開斂變怪,皆不得遁去豪末。
閣既成,主人與客,登而樂之,謀所以名其閣者。
主人復于客曰:“客亦知河伯之自多于水乎?今吾與子亦猶是也。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,陽山箭缺,累如重甗。吳王拜郊之 臺,已為黍離荊棘矣。邐迤而西,江上諸山,參錯如眉黛,吳海國、康蘄國之壁壘,亦已蕩為江流矣。下上千百年,英雄戰爭割據,杳然不可以復跡,而況于斯閣 歟?又況于吾與子以眇然之軀,寄于斯閣者歟?吾與子登斯閣也,欣然騁望,舉酒相屬,已不免啞然自笑,而何怪于人世之還而相笑與?”
客曰:“不然。于天地之間有山與湖,于山與湖之間有斯閣,于斯閣之中有吾與子。吾與子相與晞朝陽而浴夕月,釣清流而弋高風,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蛙相跨峙而以腐鼠相嚇也為何如哉?吾聞之,萬物莫不然,莫不非。因其所非而非之,是以小河伯而大海若,少仲尼而輕伯夷,因其所然而然之,則夫夔蚿之相憐,鯈魚之出游,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也。吾與子之相樂也,人世之相笑也,皆彼是之兩行也,而又何間焉?”
主人曰:“善哉!吾不能辯也。”姑以秋水名閣,而書之以為記。崇禎四年三月初五日。
楚天千里清秋,水隨天去秋無際。遙岑遠目,獻愁供恨,玉簪螺髻。落日樓頭,斷鴻聲里,江南游子。把吳鉤看了,欄桿拍遍,無人會,登臨意。(欄桿 一作:闌干) 休說鱸魚堪膾,盡西風,季鷹歸未?求田問舍,怕應羞見,劉郎才氣。可惜流年,憂愁風雨,樹猶如此!倩何人喚取,紅巾翠袖,揾英雄淚!(膾 同:鲙)
邑中園亭,仆皆為賦此詞。一日,獨坐停云,水聲山色,競來相娛。意溪山欲援例者,遂作數語,庶幾仿佛淵明思親友之意云。
甚矣吾衰矣。悵平生、交游零落,只今余幾!白發空垂三千丈,一笑人間萬事。問何物、能令公喜?我見青山多嫵媚,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。情與貌,略相似。 一尊搔首東窗里。想淵明、停云詩就,此時風味。江左沉酣求名者,豈識濁醪妙理。回首叫、云飛風起。不恨古人吾不見,恨古人不見吾狂耳。知我者,二三子。
會作鳳山宰,悠悠水利垂。天公將福報,再賜玉麟兒。
夫人稟五常,士兼百行,邪正有別,曲直不同。若邪曲者,人之所賤,而小人之道也;正直者,人之所貴,而君子之德也。然世多趨邪而棄正,不踐君子之跡,而行由小人者,何哉?語曰:“直如弦,死道邊;曲如鉤,反封侯。”故寧順從以保吉,不違忤以受害也。況史之為務,申以勸誡,樹之風聲。其有賊臣逆子,淫君亂主,茍直書其事,不掩其瑕,則穢跡彰于一朝,惡名被于千載。言之若是,吁可畏乎!
夫為于可為之時則從,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兇。如董狐之書法不隱,趙盾之為法受屈,彼我無忤,行之不疑,然后能成其良直,擅名今古。至若齊史之書崔弒,馬遷之述漢非,韋昭仗正于吳朝,崔浩犯諱于魏國,或身膏斧鉞,取笑當時;或書填坑窖,無聞后代。夫世事如此,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,勵其匪躬之節,蓋亦難矣。是以張儼發憤,私存《嘿記》之文;孫盛不平,竊撰遼東之本。以茲避禍,幸獲兩全。足以驗世途之多隘,知實錄之難遇耳。
然則歷考前史,征諸直詞,雖古人糟粕,真偽相亂,而披沙揀金,有時獲寶。案金行在歷,史事尤多。當宣、景開基之始,曹、馬構紛之際,或列營渭曲,見屈武侯,或發仗云臺,取傷成濟。陳壽、王隱,咸杜口而無言,陸機、虞預,各棲毫而靡述。至習鑿齒,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,抽戈犯蹕之言。歷代厚誣,一朝始雪。考斯人之書事,蓋近古之遺直歟?次有宋孝王《風俗傳》、王劭《齊志》,其敘述當時,亦務在審實。案于時河朔王公,箕裘未隕;鄴城將相,薪構仍存。而二子書其所諱,曾無憚色。剛亦不吐,其斯人歟?
蓋烈士徇名,壯夫重氣,寧為蘭摧玉折,不作瓦礫長存。若南、董之仗氣直書,不避強御;韋、崔之肆情奮筆,無所阿容。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,而遺芳余烈,人到于今稱之。與夫王沈《魏書》,假回邪以竊位,董統《燕史》,持諂媚以偷榮,貫三光而洞九泉,曾未足喻其高下也。
鯤身沙似雪,漁火夜團團。掩映星千點,斜聯月半闌。
微明含宿霧,列焰照回瀾。影拂寥天靜,光橫極浦寒。
遙瞻依水曲,細數隱江干。海國恬熙日,頻聞唱晚歡。
項脊軒,舊南閣子也。室僅方丈,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,塵泥滲漉,雨澤下注;每移案,顧視無可置者。又北向,不能得日,日過午已昏。余稍為修葺,使不上漏。前辟四窗,垣墻周庭,以當南日,日影反照,室始洞然。又雜植蘭桂竹木于庭,舊時欄楯,亦遂增勝。借書滿架,偃仰嘯歌,冥然兀坐,萬籟有聲;而庭階寂寂,小鳥時來啄食,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,明月半墻,桂影斑駁,風移影動,珊珊可愛。(借書 一作:積書;階寂寂 一作:堦寂寂)
然余居于此,多可喜,亦多可悲。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。迨諸父異爨,內外多置小門墻,往往而是,東犬西吠,客逾庖而宴,雞棲于廳。庭中始為籬,已為墻,凡再變矣。家有老嫗,嘗居于此。嫗,先大母婢也,乳二世,先妣撫之甚厚。室西連于中閨,先妣嘗一至。嫗每謂余曰:“某所,而母立于茲。”嫗又曰:“汝姊在吾懷,呱呱而泣;娘以指叩門扉曰:‘兒寒乎?欲食乎?’吾從板外相為應答。”語未畢,余泣,嫗亦泣。余自束發讀書軒中,一日,大母過余曰:“吾兒,久不見若影,何竟日默默在此,大類女郎也?”比去,以手闔門,自語曰:“吾家讀書久不效,兒之成,則可待乎!”頃之,持一象笏至,曰:“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,他日汝當用之!”瞻顧遺跡,如在昨日,令人長號不自禁。(內外多置小門墻,往往而是 一作:內外多置小門,墻往往而是)
軒東故嘗為廚,人往,從軒前過。余扃牖而居,久之,能以足音辨人。軒凡四遭火,得不焚,殆有神護者。
項脊生曰:“蜀清守丹穴,利甲天下,其后秦皇帝筑女懷清臺;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,諸葛孔明起隴中。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,世何足以知之,余區區處敗屋中,方揚眉、瞬目,謂有奇景。人知之者,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?”
余既為此志,后五年,吾妻來歸,時至軒中,從余問古事,或憑幾學書。吾妻歸寧,述諸小妹語曰:“聞姊家有閣子,且何謂閣子也?”其后六年,吾妻死,室壞不修。其后二年,余久臥病無聊,乃使人復葺南閣子,其制稍異于前。然自后余多在外,不常居。
庭有枇杷樹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蓋矣。
先妣周孺人,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。年十六年來歸。逾年生女淑靜,淑靜者大姊也;期而生有光;又期而生女子,殤一人,期而不育者一人;又逾年生有尚,妊十二月;逾年,生淑順;一歲,又生有功。有功之生也,孺人比乳他子加健。然數顰蹙顧諸婢曰:“吾為多子苦!”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,曰:“飲此,后妊不數矣。”孺人舉之盡,喑不能言。
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,孺人卒。諸兒見家人泣,則隨之泣。然猶以為母寢也,傷哉!于是家人延畫工畫,出二子,命之曰:鼻以上畫有光,鼻以下畫大姊。以二子肖母也。
孺人諱桂。外曾祖諱明。外祖諱行,太學生。母何氏,世居吳家橋,去縣城東南三十里;由千墩浦而南,直橋并小港以東,居人環聚,盡周氏也。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,敦尚簡實;與人姁姁說村中語,見子弟甥侄無不愛。
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;入城則緝纑,燈火熒熒,每至夜分。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。孺人不憂米鹽,乃勞苦若不謀夕。冬月爐火炭屑,使婢子為團,累累暴階下。室靡棄物,家無閑人。兒女大者攀衣,小者乳抱,手中紉綴不輟。戶內灑然。遇僮奴有恩,雖至棰楚,皆不忍有后言。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,率人人得食。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,皆喜。有光七歲,與從兄有嘉入學,每陰風細雨,從兄輒留,有光意戀戀,不得留也。孺人中夜覺寢,促有光暗誦《孝經》即熟讀,無一字齟齬,乃喜。
孺人卒,母何孺人亦卒。周氏家有羊狗之痾。舅母卒,四姨歸顧氏,又卒,死三十人而定。惟外祖與二舅存。
孺人死十一年,大姊歸王三接,孺人所許聘者也。十二年,有光補學官弟子,十六年而有婦,孺人所聘者也。期而抱女,撫愛之,益念孺人。中夜與其婦泣,追惟一二,仿佛如昨,馀則茫然矣。世乃有無母之人,天乎?痛哉!
婢,魏孺人媵也。生女如蘭,如蘭死,又生一女,亦死。予嘗寓京師,作《如蘭母》詩。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。葬虛丘。事我而不卒,命也夫!
婢初媵時,年十歲,垂雙鬟,曳深綠布裳。一日天寒,爇火煮荸薺熟,婢削之盈甌,予入自外,取食之,婢持去不與。魏孺人笑之。孺人每令婢倚幾旁飯,即飯,目眶冉冉動,孺人又指予以為笑。
回思是時,奄忽便已十年。吁,可悲也已!
浮圖文瑛居大云庵,環水,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滄浪亭記》,曰:“昔子美之記,記亭之勝也。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。”
余曰:昔吳越有國時,廣陵王鎮吳中,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;其外戚孫承祐,亦治園于其偏。迨淮海納土,此園不廢。蘇子美始建滄浪亭,最后禪者居之: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。有庵以來二百年,文瑛尋古遺事,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余: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。
夫古今之變,朝市改易。嘗登姑蘇之臺,望五湖之渺茫,群山之蒼翠,太伯、虞仲之所建,闔閭、夫差之所爭,子胥、種、蠡之所經營,今皆無有矣。庵與亭何為者哉?雖然,錢镠因亂攘竊,保有吳越,國富兵強,垂及四世。諸子姻戚,乘時奢僭,宮館苑囿,極一時之盛。而子美之亭,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。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,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,則有在矣。
文瑛讀書喜詩,與吾徒游,呼之為滄浪僧云。
吳、長洲二縣,在郡治所,分境而治。而郡西諸山,皆在吳縣。其最高者,穹窿、陽山、鄧尉、西脊、銅井。而靈巖,吳之故宮在焉,尚有西子之遺跡。若虎丘、劍池及天平、尚方、支硎,皆勝地也。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,七十二峰沉浸其間,則海內之奇觀矣。
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,未及三年,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。君之為縣,有惠愛,百姓扳留之,不能得,而君亦不忍于其民。由是好事者繪《吳山圖》以為贈。
夫令之于民,誠重矣。令誠賢也,其地之山川草木,亦被其澤而有榮也;令誠不賢也,其地之山川草木,亦被其殃而有辱也。君于吳之山川,蓋增重矣。異時吾民將擇勝于巖巒之間,尸祝于浮屠、老子之宮也,固宜。而君則亦既去矣,何復惓惓于此山哉?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,至以為《思黃州》詩,子瞻為黃人刻之于石。然后知賢者于其所至,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,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。
君今去縣已三年矣。一日,與余同在內庭,出示此圖,展玩太息,因命余記之,噫!君之于吾吳有情如此,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!
太湖,東南巨浸也,廣五百里,群峰出于波濤之間以百數。而重涯別塢,幽谷曲隈,無非仙靈之所棲息。天下之山,得水而悅,水或束隘迫狹,不足以盡山之奇;天下之水,得山而止,山或孤孑卑稚,不足以極水之趣。太湖漭淼澒洞,沉浸諸山,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。意惟海外絕島勝是,中州無有也。故凡奔涌屏列于湖之濱者,皆挾湖以為勝。
自錫山過五里湖,得寶界山,在洞庭之北,夫椒、湫山之間,仲山王先生居之。先生蚤歲棄官,而其子鑒始登第,亦告歸,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。因長洲陸君,來請予為山居之記。
余未至寶界也,嘗讀書萬峰山,盡得湖濱諸山之景。雖面勢不同,無不挾湖以為勝,而馬跡長興,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,則所謂寶界者,庶幾望見之。昔王右丞輞川別墅,其詩畫之妙,至今可以想見其處。仲山之居,豈減華子岡、欹湖諸奇勝?而千里湖山,豈藍田之所有哉?摩詰清思逸韻,出塵壒之外。而天寶之末,顧不能自引決,以濡羯胡之腥膻。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,一失足遂不可浣,如摩詰,令人千載有遺恨也。今仲山父子嘉遁于明時,何可及哉!何可及哉!
杏花書屋,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。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,謫沅、湘時,嘗夢居一室,室旁杏花爛漫,諸子讀書其間,聲瑯然出戶外。嘉靖初,起官陟憲使,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,今所居宅是也。公指其后隙地謂允曰:“他日當建一室,名之為杏花書屋,以志吾夢云。”
公后遷南京刑部右侍郎,不及歸而沒于金陵。孺允兄弟數見侵侮,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。如是數年,始獲安居。至嘉靖二十年,孺允葺公所居堂,因于園中構屋五楹,貯書萬卷,以公所命名,揭之楣間,周環藝以花果竹木。方春時,杏花粲發,恍如公昔年夢中矣。而回思洞庭木葉、芳洲杜若之間,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。登其室,思其人,能不慨然矣乎!
昔唐人重進士科,士方登第時,則長安杏花盛開,故杏園之宴,以為盛事。今世試進士,亦當杏花時,而士之得第,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。此世俗不忘于榮名者為然。公以言事忤天子,間關嶺海十馀年,所謂鐵石心腸,于富貴之念灰滅盡矣;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。蓋古昔君子,愛其國家,不獨盡瘁其躬而已;至于其后,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。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。
今去公之歿,曾幾何時,向之所與同進者,一時富貴翕赫,其后有不知所在者。孺允兄弟雖蠖屈于時,而人方望其大用:而諸孫皆秀發,可以知《詩》《書》之澤也。《詩》曰:“自今以始,歲其有,君子有谷,貽孫子。于胥樂兮!”吾于周氏見之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