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舒伯源自雙溪口度橋登高山望幽谷諸峰賦八絕 其二
坐石弄芳草,渡溪行翠微。西峰月未上,獨自看云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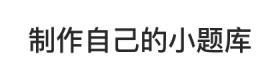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坐石弄芳草,渡溪行翠微。西峰月未上,獨自看云歸。
慈懷寄言盼兒歸,十載閨思夢寐依。養女休嗟道旁棄,隨夫不怨室中饑。
西來宦轍年頻徙,南望鄉關日久違。為說平安憑遠報,長途猶恐信音稀。
君未能歸妾忍歸,幽懷好共話因依。敢云兒女來時累,莫忘夫妻去日饑。
夢里思量還意合,行間言語與心違。玉門關外寒威重,爭奈春風到此稀。
兒時未識賦于歸,只道深閨母是依。一自催妝癡若夢,幾番離別怒如饑。
畫眉猶為顏容惜,分手何堪色笑違。讀罷新詩含淚和,淚痕多覺墨痕稀。
虎丘,中秋游者尤盛。士女傾城而往,笙歌笑語,填山沸林,終夜不絕。遂使丘壑化為酒場,穢雜可恨。
予初十日到郡,連夜游虎丘,月色甚美,游人尚稀,風亭月榭間,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,亦復不惡。然終不若山空人靜,獨往會心。
嘗秋夜坐釣月磯,昏黑無往來,時聞風鐸,及佛燈隱現林梢而已。
又今年春中,與無際偕訪仲和于此。夜半月出無人,相與趺坐石臺,不復飲酒,亦不復談,以靜意對之,覺悠悠欲與清景俱往也。
生平過虎丘才兩度,見虎丘本色耳。友人徐聲遠詩云:“獨有歲寒好,偏宜夜半游。”真知言哉!
出西直門,過高梁橋,可十余里,至元君祠。折而北,有平堤十里,夾道皆古柳,參差掩映。澄湖百頃,一望渺然。西山匌匒,與波光上下。遠見功德古剎及玉泉亭榭,朱門碧瓦,青林翠嶂,互相綴發。湖中菰蒲零亂,鷗鷺翩翻,如在江南畫圖中。
予信宿金山及碧云、香山。是日,跨蹇而歸。由青龍橋縱轡堤上。晚風正清,湖煙乍起,嵐潤如滴,柳嬌欲狂,顧而樂之,殆不能去。
先是,約孟旋、子將同游,皆不至,予慨然獨行。子將挾西湖為己有,眼界則高矣,顧穩踞七香城中,傲予此行,何也?書寄孟陽諸兄之在西湖者,一笑。
六國破滅,非兵不利,戰不善,弊在賂秦。賂秦而力虧,破滅之道也。或曰:六國互喪,率賂秦耶?曰:不賂者以賂者喪。蓋失強援,不能獨完。故曰:弊在賂秦也。
秦以攻取之外,小則獲邑,大則得城。較秦之所得,與戰勝而得者,其實百倍;諸侯之所亡,與戰敗而亡者,其實亦百倍。則秦之所大欲,諸侯之所大患,固不在戰矣。思厥先祖父,暴霜露,斬荊棘,以有尺寸之地。子孫視之不甚惜,舉以予人,如棄草芥。今日割五城,明日割十城,然后得一夕安寢。起視四境,而秦兵又至矣。然則諸侯之地有限,暴秦之欲無厭,奉之彌繁,侵之愈急。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。至于顛覆,理固宜然。古人云:“以地事秦,猶抱薪救火,薪不盡,火不滅。”此言得之。
齊人未嘗賂秦,終繼五國遷滅,何哉?與嬴而不助五國也。五國既喪,齊亦不免矣。燕趙之君,始有遠略,能守其土,義不賂秦。是故燕雖小國而后亡,斯用兵之效也。至丹以荊卿為計,始速禍焉。趙嘗五戰于秦,二敗而三勝。后秦擊趙者再,李牧連卻之。洎牧以讒誅,邯鄲為郡,惜其用武而不終也。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,可謂智力孤危,戰敗而亡,誠不得已。向使三國各愛其地,齊人勿附于秦,刺客不行,良將猶在,則勝負之數,存亡之理,當與秦相較,或未易量。
嗚呼!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,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,并力西向,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悲夫!有如此之勢,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,日削月割,以趨于亡。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!
夫六國與秦皆諸侯,其勢弱于秦,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。茍以天下之大,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,是又在六國下矣。
榆莢雨疏還養神,楝花風急欲侵真。偷藏翠葉棲邊鳥,戲摘赪葩醉后人。
細看始能知絕韻,偶飛深為惜嬌塵。對花我欲長歌舞,怕數階蓂幾莢真。
為將之道,當先治心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,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,然后可以制利害,可以待敵。
凡兵上義;不義,雖利勿動。非一動之為利害,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義可以怒士,士以義怒,可與百戰。
凡戰之道,未戰養其財,將戰養其力,既戰養其氣,既勝養其心。謹烽燧,嚴斥堠,使耕者無所顧忌,所以養其財;豐犒而優游之,所以養其力;小勝益急,小挫益厲,所以養其氣;用人不盡其所欲為,所以養其心。故士常蓄其怒、懷其欲而不盡。怒不盡則有馀勇,欲不盡則有馀貪。故雖并天下,而士不厭兵,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。不養其心,一戰而勝,不可用矣。
凡將欲智而嚴,凡士欲愚。智則不可測,嚴則不可犯,故士皆委己而聽命,夫安得不愚?夫惟士愚,而后可與之皆死。
凡兵之動,知敵之主,知敵之將,而后可以動于險。鄧艾縋兵于蜀中,非劉禪之庸,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,彼固有所侮而動也。故古之賢將,能以兵嘗敵,而又以敵自嘗,故去就可以決。
凡主將之道,知理而后可以舉兵,知勢而后可以加兵,知節而后可以用兵。知理則不屈,知勢則不沮,知節則不窮。見小利不動,見小患不避,小利小患,不足以辱吾技也,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養技而自愛者,無敵于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,一靜可以制百動。
兵有長短,敵我一也。敢問:“吾之所長,吾出而用之,彼將不與吾校;吾之所短,吾蔽而置之,彼將強與吾角,奈何?”曰:“吾之所短,吾抗而暴之,使之疑而卻;吾之所長,吾陰而養之,使之狎而墮其中。此用長短之術也。”
善用兵者,使之無所顧,有所恃。無所顧,則知死之不足惜;有所恃,則知不至于必敗。尺箠當猛虎,奮呼而操擊;徒手遇蜥蜴,變色而卻步,人之情也。知此者,可以將矣。袒裼而案劍,則烏獲不敢逼;冠胄衣甲,據兵而寢,則童子彎弓殺之矣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,則力有馀矣。
芳蘭氣味海棠神,并作庭前錦樣真。風葉似來遺佩女,露腮如遇泣珠人。
數枝宿艷欺山日,百歲浮生棲草塵。正是及辰君不賞,莫教春去卻懷春。
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靜者,乃能見微而知著。月暈而風,礎潤而雨,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,理勢之相因,其疏闊而難知,變化而不可測者,孰與天地陰陽之事。而賢者有不知,其故何也?好惡亂其中,而利害奪其外也!
昔者,山巨源見王衍曰:“誤天下蒼生者,必此人也!”郭汾陽見盧杞曰: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孫無遺類矣!”自今而言之,其理固有可見者。以吾觀之,王衍之為人,容貌言語,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。然不忮不求,與物浮沉。使晉無惠帝,僅得中主,雖衍百千,何從而亂天下乎?盧杞之奸,固足以敗國。然而不學無文,容貌不足以動人,言語不足以眩世,非德宗之鄙暗,亦何從而用之?由是言之,二公之料二子,亦容有未必然也!
今有人,口誦孔、老之言,身履夷、齊之行,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,相與造作言語,私立名字,以為顏淵、孟軻復出,而陰賊險狠,與人異趣。是王衍、盧杞合而為一人也。其禍豈可勝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,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,衣臣虜之衣。食犬彘之食,囚首喪面,而談詩書,此豈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,鮮不為大奸慝,豎刁、易牙、開方是也。以蓋世之名,而濟其未形之患。雖有愿治之主,好賢之相,猶將舉而用之。則其為天下患,必然而無疑者,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孫子曰:“善用兵者,無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,則吾言為過,而斯人有不遇之嘆。孰知禍之至于此哉?不然。天下將被其禍,而吾獲知言之名,悲夫!
胭脂為骨暈生神,不許緋桃更逼真。疑謫艷陽天上質,絕勝佳麗水邊人。
染來香骨薔微露,點破紅腮柳絮塵。莫向花時不歡賞,人生能見幾番春。
萬姿千態逞嬌神,誰更嬌神與賽真。樓外吹簫秦弄玉,帳中鳴佩衛夫人。
金錢卜遠微聞語,羅襪凌波暗惹塵。始信此為傾國色,與君同占可憐春。
管仲相桓公,霸諸侯,攘夷狄,終其身齊國富強,諸侯不叛。管仲死,豎刁、易牙、開方用,桓公薨于亂,五公子爭立,其禍蔓延,訖簡公,齊無寧歲。
夫功之成,非成于成之日,蓋必有所由起;禍之作,不作于作之日,亦必有所由兆。故齊之治也,吾不曰管仲,而曰鮑叔;及其亂也,吾不曰豎刁、易牙、開方,而曰管仲。何則?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子,彼固亂人國者,顧其用之者,桓公也。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兇,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。彼桓公何人也?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,管仲也。仲之疾也,公問之相。當是時也,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。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、易牙、開方三子非人情,不可近而已。
嗚呼!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?仲與桓公處幾年矣,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?桓公聲不絕于耳,色不絕于目,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。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,徒以有仲焉耳。一日無仲,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。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?夫齊國不患有三子,而患無仲。有仲,則三子者,三匹夫耳。不然,天下豈少三子之徒?雖桓公幸而聽仲,誅此三人,而其余者,仲能悉數而去之耶?嗚呼!仲可謂不知本者矣!因桓公之問,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,則仲雖死,而齊國未為無仲也。夫何患?三子者不言可也。
五伯莫盛于桓、文,文公之才,不過桓公,其臣又皆不及仲;靈公之虐,不如孝公之寬厚。文公死,諸侯不敢叛晉,晉襲文公之余威,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。何者?其君雖不肖,而尚有老成人焉。桓公之薨也,一亂涂地,無惑也,彼獨恃一管仲,而仲則死矣。
夫天下未嘗無賢者,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。桓公在焉,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,吾不信也。仲之書有記其將死,論鮑叔、賓胥無之為人,且各疏其短,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,而又逆知其將死,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。吾觀史?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,故有身后之諫;蕭何且死,舉曹參以自代。大臣之用心,固宜如此也。夫國以一人興,以一人亡,賢者不悲其身之死,而憂其國之衰,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。彼管仲者,何以死哉?
酷愛園丁技獨神,染來隨意卻能真。奇香滿院若薰麝,嬌影隔簾如覘人。
三五朵皆呈絕色,百千花盡避清塵。有因自與東風好,不肯吹殘枝上春。
木之生,或蘗而殤,或拱而夭;幸而至于任為棟梁,則伐;不幸而為風之所拔,水之所漂,或破折或腐;幸而得不破折不腐,則為人之所材,而有斧斤之患。其最幸者,漂沉汩沒于湍沙之間,不知其幾百年,而其激射嚙食之馀,或仿佛于山者,則為好事者取去,強之以為山,然后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。而荒江之濆,如此者幾何,不為好事者所見,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,何可勝數?則其最幸者之中,又有不幸者焉。
予家有三峰。予每思之,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。且其孽而不殤,拱而不夭,任為棟梁而不伐;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,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,以及于斧斤之,出于湍沙之間,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,而后得至乎此,則其理似不偶然也。
然予之愛之,則非徒愛其似山,而又有所感焉;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。予見中峰,魁岸踞肆,意氣端重,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。二峰者,莊栗刻削,凜乎不可犯,雖其勢服于中峰,而岌然決無阿附意。吁!其可敬也夫!其可以有所感也夫!
內翰執事:洵布衣窮居,嘗竊有嘆,以為天下之人,不能皆賢,不能皆不肖。故賢人君子之處于世,合必離,離必合。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,而范公在相府,富公為樞密副使,執事與余公、蔡公為諫官,尹公馳騁上下,用力于兵革之地。方是之時,天下之人,毛發絲粟之才,紛紛然而起,合而為一。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,不足以自奮于其間,退而養其心,幸其道之將成,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。不幸道未成,而范公西,富公北,執事與余公、蔡公分散四出,而尹公亦失勢,奔走于小官。洵時在京師,親見其事,忽忽仰天嘆息,以為斯人之去,而道雖成,不復足以為榮也。既復自思,念往者眾君子之進于朝,其始也,必有善人焉推之;今也,亦必有小人焉間之。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,則已矣。如其不然也,吾何憂焉?姑養其心,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,何傷?退而處十年,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,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。而余公適亦有成功于南方,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于朝,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,其勢將復合為一。喜且自賀,以為道既已粗成,而果將有以發之也。既又反而思,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,蓋有六人焉,今將往見之矣。而六人者,已有范公、尹公二人亡焉,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。嗚呼,二人者不可復見矣!而所恃以慰此心者,猶有四人也,則又以自解。思其止于四人也,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,以發其心之所欲言。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,遠方寒士,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;余公、蔡公,遠者又在萬里外,獨執事在朝廷間,而其位差不甚貴,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。而饑寒衰老之病,又痼而留之,使不克自至于執事之庭。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,十年而不得見,而其人已死,如范公、尹公二人者;則四人之中,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,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!
執事之文章,天下之人莫不知之;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,愈于天下之人。何者?孟子之文,語約而意盡,不為巉刻斬絕之言,而其鋒不可犯。韓子之文,如長江大河,渾浩流轉,魚黿蛟龍,萬怪惶惑,而抑遏蔽掩,不使自露;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,蒼然之色,亦自畏避,不敢迫視。執事之文,紆余委備,往復百折,而條達疏暢,無所間斷;氣盡語極,急言竭論,而容與閑易,無艱難勞苦之態。此三者,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。惟李翱之文,其味黯然而長,其光油然而幽,俯仰揖讓,有執事之態。陸贄之文,遣言措意,切近得當,有執事之實;而執事之才,又自有過人者。蓋執事之文,非孟子、韓子之文,而歐陽子之文也。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,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;彼不知者,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。夫譽人以求其悅己,洵亦不為也;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,而不自知止者,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。
雖然,執事之名,滿于天下,雖不見其文,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。而洵也不幸,墮在草野泥涂之中。而其知道之心,又近而粗成。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,自托于執事,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、何從而信之哉?洵少年不學,生二十五歲,始知讀書,從士君子游。年既已晚,而又不遂刻意厲行,以古人自期,而視與己同列者,皆不勝己,則遂以為可矣。其后困益甚,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讀之,始覺其出言用意,與己大異。時復內顧,自思其才,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。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,取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、韓子及其他圣人、賢人之文,而兀然端坐,終日以讀之者,七八年矣。方其始也,入其中而惶然,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。及其久也,讀之益精,而其胸中豁然以明,若人之言固當然者。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。時既久,胸中之言日益多,不能自制,試出而書之。已而再三讀之,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,然猶未敢以為是也。近所為《洪范論》《史論》凡七篇,執事觀其如何?嘻!區區而自言,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,以求人之知己也。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