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
婺城攻陷西南角,三日人頭如雨落。 輕則鴻毛重泰山,志士誰能不溝壑。 胡君妻子泣如洗,我獨破涕為之喜。 既喜君能殉國危,復喜君能死知己。 生芻一束人如玉,人百其身不可贖。 與子交淺情獨深,愿言為子殺青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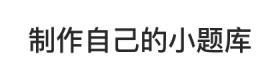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婺城攻陷西南角,三日人頭如雨落。 輕則鴻毛重泰山,志士誰能不溝壑。 胡君妻子泣如洗,我獨破涕為之喜。 既喜君能殉國危,復喜君能死知己。 生芻一束人如玉,人百其身不可贖。 與子交淺情獨深,愿言為子殺青竹。
燕地寒,花朝節后,余寒猶厲。凍風時作,作則飛沙走礫。局促一室之內,欲出不得。每冒風馳行,未百步輒返。
廿二日天稍和,偕數友出東直,至滿井。高柳夾堤,土膏微潤,一望空闊,若脫籠之鵠。于時冰皮始解,波色乍明,鱗浪層層,清澈見底,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。山巒為晴雪所洗,娟然如拭,鮮妍明媚,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。柳條將舒未舒,柔梢披風,麥田淺鬣寸許。游人雖未盛,泉而茗者,罍而歌者,紅裝而蹇者,亦時時有。風力雖尚勁,然徒步則汗出浹背。凡曝沙之鳥,呷浪之鱗,悠然自得,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。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,而城居者未之知也。
夫不能以游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,惟此官也。而此地適與余近,余之游將自此始,惡能無紀?己亥之二月也。
虎丘去城可七八里,其山無高巖邃壑,獨以近城,故簫鼓樓船,無日無之。凡月之夜,花之晨,雪之夕,游人往來,紛錯如織,而中秋為尤勝。
每至是日,傾城闔戶,連臂而至。衣冠士女,下迨蔀屋,莫不靚妝麗服,重茵累席,置酒交衢間。從千人石上至山門,櫛比如鱗,檀板丘積,樽罍云瀉,遠而望之,如雁落平沙,霞鋪江上,雷輥電霍,無得而狀。
布席之初,唱者千百,聲若聚蚊,不可辨識。分曹部署,竟以歌喉相斗,雅俗既陳,妍媸自別。未幾而搖手頓足者,得數十人而已;已而明月浮空,石光如練,一切瓦釜,寂然停聲,屬而和者,才三四輩;一簫,一寸管,一人緩板而歌,竹肉相發,清聲亮徹,聽者魂銷。比至夜深,月影橫斜,荇藻凌亂,則簫板亦不復用;一夫登場,四座屏息,音若細發,響徹云際,每度一字,幾盡一刻,飛鳥為之徘徊,壯士聽而下淚矣。
劍泉深不可測,飛巖如削。千頃云得天池諸山作案,巒壑競秀,最可觴客。但過午則日光射人,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閣亦佳,晚樹尤可觀。而北為平遠堂舊址,空曠無際,僅虞山一點在望,堂廢已久,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,欲祠韋蘇州、白樂天諸公于其中;而病尋作,余既乞歸,恐進之之興亦闌矣。山川興廢,信有時哉!
吏吳兩載,登虎丘者六。最后與江進之、方子公同登,遲月生公石上。歌者聞令來,皆避匿去。余因謂進之曰:“甚矣,烏紗之橫,皂隸之俗哉!他日去官,有不聽曲此石上者,如月!”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。虎丘之月,不知尚識余言否耶?
余少時過里肆中,見北雜劇有《四聲猿》,意氣豪達,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,題曰“天池生”,疑為元人作。后適越,見人家單幅上有署“田水月”者,強心鐵骨,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,字畫之中,宛宛可見。意甚駭之,而不知田水月為何人。
一夕坐陶太史樓,隨意抽架上書,得《闕編》詩一帙,惡楮毛書,煙煤敗黑,微有字形。稍就燈間讀之,讀未數首,不覺驚躍,急呼周望:“《闕編》何人作者,今邪古邪?”周望曰:“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。”兩人躍起,燈影下讀復叫,叫復讀,僮仆睡者皆驚起。蓋不佞生三十年,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,噫,是何相識之晚也!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,略為次第,為《徐文長傳》。
徐渭,字文長,為山陰諸生,聲名藉甚。薛公蕙校越時,奇其才,有國士之目。然數奇,屢試輒蹶。中丞胡公宗憲聞之,客諸幕。文長每見,則葛衣烏巾,縱談天下事,胡公大喜。是時公督數邊兵,威鎮東南,介胄之士,膝語蛇行,不敢舉頭,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,議者方之劉真長、杜少陵云。會得白鹿,屬文長作表,表上,永陵喜。公以是益奇之,一切疏計,皆出其手。文長自負才略,好奇計,談兵多中,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。然竟不偶。
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,遂乃放浪曲糵,恣情山水,走齊、魯、燕、趙之地,窮覽朔漠。其所見山奔海立、沙起云行、雨鳴樹偃、幽谷大都、人物魚鳥,一切可驚可愕之狀,一一皆達之于詩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,英雄失路、托足無門之悲,故其為詩,如嗔如笑,如水鳴峽,如種出土,如寡婦之夜哭,羈人之寒起。雖其體格時有卑者,然匠心獨出,有王者氣,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識,氣沉而法嚴,不以摸擬損才,不以議論傷格,韓、曾之流亞也。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,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,文長皆叱而奴之,故其名不出于越,悲夫!喜作書,筆意奔放如其詩,蒼勁中姿媚躍出,歐陽公所謂“妖韶女老,自有余態”者也。間以其余,旁溢為花鳥,皆超逸有致。
卒以疑殺其繼室,下獄論死。張太史元汴力解,乃得出。晚年憤益深,佯狂益甚,顯者至門,或拒不納。時攜錢至酒肆,呼下隸與飲。或自持斧擊破其頭,血流被面,頭骨皆折,揉之有聲。或以利錐錐其兩耳,深入寸余,竟不得死。周望言:“晚歲詩文益奇,無刻本,集藏于家。”余同年有官越者,托以抄錄,今未至。余所見者,《徐文長集》《闕編》二種而已。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,抱憤而卒。
石公曰:“先生數奇不已,遂為狂疾;狂疾不已,遂為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騷困苦,未有若先生者也。雖然,胡公間世豪杰,永陵英主,幕中禮數異等,是胡公知有先生矣;表上,人主悅,是人主知有先生矣,獨身未貴耳。先生詩文崛起,一掃近代蕪穢之習,百世而下,自有定論,胡為不遇哉?”
梅客生嘗寄予書曰:“文長吾老友,病奇于人,人奇于詩。”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。無之而不奇,斯無之而不奇也。悲夫!
西湖最盛,為春為月。一日之盛,為朝煙,為夕嵐。
今歲春雪甚盛,梅花為寒所勒,與杏桃相次開發,尤為奇觀。石簣數為余言:“傅金吾園中梅,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,急往觀之。”余時為桃花所戀,竟不忍去。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,綠煙紅霧,彌漫二十余里。歌吹為風,粉汗為雨,羅紈之盛,多于堤畔之草,艷冶極矣。
然杭人游湖,止午、未、申三時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,山嵐設色之妙,皆在朝日始出,夕舂未下,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,花態柳情,山容水意,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山僧游客受用,安可為俗士道哉?
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,由莊至顛,可二十余里。
凡山深辟者多荒涼,峭削者鮮迂曲;貌古則鮮妍不足,骨大則玲瓏絕少,以至山高水乏,石峻毛枯:凡此皆山之病。
天目盈山皆壑,飛流淙淙,若萬匹縞,一絕也。石色蒼潤,石骨奧巧,石徑曲折,石壁竦峭,二絕也。雖幽谷縣巖,庵宇皆精,三絕也。余耳不喜雷,而天目雷聲甚小,聽之若嬰兒聲,四絕也。曉起看云,在絕壑下,白凈如綿,奔騰如浪,盡大地作琉璃海,諸山尖出云上若萍,五絕也。然云變態最不常,其觀奇甚,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。山樹大者,幾四十圍,松形如蓋,高不逾數尺,一株直萬余錢,六絕也。頭茶之香者,遠勝龍井,筍味類紹興破塘,而清遠過之,七絕也。余謂大江之南,修真棲隱之地,無逾此者,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。
宿幻住之次日,晨起看云,巳后登絕頂,晚宿高峰死關。次日,由活埋庵尋舊路而下。數日晴霽甚,山僧以為異,下山率相賀。山中僧四百余人,執禮甚恭,爭以飯相勸。臨行,諸僧進曰: “荒山僻小,不足當巨目,奈何?”余曰:“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,山僧不勞過謙,某亦不敢面譽。”因大笑而別。
從山門右折,得石徑。數步聞疾雷聲,心悸。山僧曰:“此瀑聲也。”
疾趨,度石罅,瀑見。石青削,不容寸膚,三面皆郛立。瀑行青壁間,撼山掉谷,噴雪直下,怒石橫激如虹,忽卷掣折而后注,水態愈偉,山行之極觀也。
游人坐欹巖下望,以面受沫,乍若披絲,虛空皆緯,至飛雨瀉崖,而猶不忍去。
暮歸,各賦詩。所目既奇,思亦變幻,恍惚牛鬼蛇神,不知作何等語。時夜已午, 魈呼虎號之聲,如在床幾間。彼此諦觀,須眉毛發,種種皆豎,俱若鬼矣。
不孝完淳今日死矣!以身殉父,不得以身報母矣!痛自嚴君見背,兩易春秋,冤酷日深,艱辛歷盡。本圖復見天日,以報大仇,恤死榮生,告成黃土;奈天不佑我,鐘虐先朝,一旅才興,便成齏粉。去年之舉,淳已自分必死,誰知不死,死于今日也。斤斤延此二年之命,菽水之養無一日焉。致慈君托跡于空門,生母寄生于別姓,一門漂泊,生不得相依,死不得相問;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:不孝之罪,上通于天!
嗚呼!雙慈在堂,下有妹女,門祚衰薄,終鮮兄弟。淳一死不足惜,哀哀八口,何以為生?雖然,已矣!淳之身,父之所遺;淳之身,君之所用。為父為君,死亦何負于雙慈!但慈君推干就濕,教禮習詩,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,千古所難,大恩未酬,令人痛絕。——慈君托之義融女兄,生母托之昭南女弟。
淳死之后,新婦遺腹得雄,便以為家門之幸。如其不然,萬勿置后!會稽大望,至今而零極矣!節義文章,如我父子者幾人哉?立一不肖后如西銘先生,為人所詬笑,何如不立之為愈耶!嗚呼!大造茫茫,總歸無后。有一日中興再造,則廟食千秋,豈止麥飯豚蹄,不為餒鬼而已哉!若有妄言立后者,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,決不肯舍!
兵戈天地,淳死后,亂且未有定期。雙慈善保玉體,無以淳為念。二十年后,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矣!勿悲勿悲!相托之言,慎勿相負!武功甥將來大器,家事盡以委之。寒食盂蘭,一杯清酒,一盞寒燈,不至作若敖之鬼,則吾愿畢矣!新婦結褵二年,賢孝素著。武功甥好為我善待之。亦武功渭陽情也。
語無倫次,將死言善。痛哉痛哉!人生孰無死?貴得死所耳!父得為忠臣,子得為孝子。含笑歸太虛,了我分內事。大道本無生,視身若敝屣。但為氣所激,緣悟天人理。惡夢十七年,報仇于來世。神游天地間,可以無愧矣!
復楚情何極,亡秦氣未平。 雄風清角勁,落日大旗明。 縞素酬家國,戈船決死生! 胡笳千古恨,一片月臨城。
戰苦難酬國,仇深敢憶家? 一身存漢臘,滿目盡胡沙。 落月翻旗影,清霜冷劍花。 六軍渾散盡,半夜起悲笳。
一旅同仇誼,三秋故主懷。 將星沉左輔,卿月隱中臺。 東閣塵賓幕,西征愧賦才。 月明笳鼓切,今夜為誰哀。
將壇醇酒冰漿細,元夜邀賓燈火新。 直待清霄寒吐月,休教白發老侵人。
香翻桂影燭光薄,紅沁榆階寶靨勻。 群品欣欣增氣色,太平依舊獨閑身。
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,道此入玉河。白練千匹,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。堤在水中,兩波相夾。綠楊四行,樹古葉繁,一樹之蔭,可覆數席,垂線長丈馀。
岸北佛廬道院甚眾,朱門紺殿,亙數十里。對面遠樹,高下攢簇,間以水田,西山如螺髻,出于林水之間。
極樂寺去橋可三里,路徑亦佳。馬行綠蔭中,若張蓋。殿前剔牙松數株,松身鮮翠嫩黃,斑剝若大魚鱗,大可七八圍許。
暇日,曾與黃思立諸公游此。予弟中郎云:“此地小似錢塘蘇堤。”思立亦以為然。余因嘆西湖勝景,入夢已久,何日掛進賢冠,作六橋下客子,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?是日分韻,各賦一詩而別。
六王畢,四海一,蜀山兀,阿房出。覆壓三百余里,隔離天日。驪山北構而西折,直走咸陽。二川溶溶,流入宮墻。五步一樓,十步一閣;廊腰縵回,檐牙高啄;各抱地勢,鉤心斗角。盤盤焉,囷囷焉,蜂房水渦,矗不知其幾千萬落。長橋臥波,未云何龍?復道行空,不霽何虹?高低冥迷,不知西東。歌臺暖響,春光融融;舞殿冷袖,風雨凄凄。一日之內,一宮之間,而氣候不齊。(不知其 一作:不知乎;西東 一作:東西)
妃嬪媵嬙,王子皇孫,辭樓下殿,輦來于秦。朝歌夜弦,為秦宮人。明星熒熒,開妝鏡也;綠云擾擾,梳曉鬟也;渭流漲膩,棄脂水也;煙斜霧橫,焚椒蘭也。雷霆乍驚,宮車過也;轆轆遠聽,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肌一容,盡態極妍,縵立遠視,而望幸焉。有不見者,三十六年。燕趙之收藏,韓魏之經營,齊楚之精英,幾世幾年,剽掠其人,倚疊如山。一旦不能有,輸來其間。鼎鐺玉石,金塊珠礫,棄擲邐迤,秦人視之,亦不甚惜。(有不見者 一作:有不得見者)
嗟乎!一人之心,千萬人之心也。秦愛紛奢,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盡錙銖,用之如泥沙?使負棟之柱,多于南畝之農夫;架梁之椽,多于機上之工女;釘頭磷磷,多于在庾之粟粒;瓦縫參差,多于周身之帛縷;直欄橫檻,多于九土之城郭;管弦嘔啞,多于市人之言語。使天下之人,不敢言而敢怒。獨夫之心,日益驕固。戍卒叫,函谷舉,楚人一炬,可憐焦土!
嗚呼!滅六國者六國也,非秦也;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。嗟乎!使六國各愛其人,則足以拒秦;使秦復愛六國之人,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,誰得而族滅也?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鑒之,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。
新愁因甚多?淺黛教誰畫?倦將珊枕欹,款要朱扉亞。月明閑照綠窗紗,酒 冷重溫白玉。五花驄系何處垂揚下,少年心虧負殺、虧負殺。不恨你個冤家, 高燒銀蠟,寬鋪繡榻,今夜來么? 尋致爭不致爭,既言定先言定。論至誠俺至誠,你薄幸誰薄幸?豈不舉頭三 尺有神明,忘義多應當罪名。海神廟見有他為證,似王魁負桂英。磣可可海誓山 盟。縷帶難逃命,裙刀上更自刑,活取了個年少書生。
黃薔薇過慶元貞燕燕別無甚孝順,哥哥行在意殷勤。三納子藤箱兒 問肯,便待要錦帳羅幃就親。唬得我驚急列驀出臥房門,他措支刺扯住我皂腰裙, 我軟兀刺好話兒倒溫存:“一來怕夫人,情性哏,二來怕誤妾百年身。” 又不曾看生見長,便這般割肚牽腸。喚奶奶酩子里賜賞,撮醋醋孩兒弄璋。 斷送得他蕭蕭鞍馬出咸陽,只因他重重恩愛在昭陽,引惹得紛紛戈戟鬧漁陽。哎, 三郎,睡海棠,都則為一曲舞霓裳。
吳有儒曰徐孟祥氏,讀書績文,志行高潔,家光福山中。相從而學問者甚夥,其聲名隱然于郡國。縉紳大夫游于西山,必造其廬焉。孟祥嘗結廬數椽,覆以白茅,不事華飾,惟粉堊其中,宛然雪屋也。既落成,而天適雨雪,遂以“雪屋”名之。范陽盧舍人為古隸以扁之,縉紳之交于孟祥者,為詩以歌詠之,征予為之記。
夫玄冥司令,草木消歇閉塞,成冬之時。天地積陰之氣,濕而為雨,寒而為雪,緩緩而下,一白千里,遍覆于山林大地。萬物埋沒無所見,其生意不幾息乎?孰知生意反寓于其中也。故冬至之節,居小雪之后,大雪之前,而一陽已生于五陰之下矣。由是臘中有雪,則來春有收,人亦五疾疹之患。是雪也,非獨以其色之潔白為可尚也,蓋有生意弭災之功在焉。太古之人,或巢于木,或處于穴。木處而顛,土處而病也。圣人為屋以居,冀免乎二者之患而已矣,初未嘗有后世華侈之飾也。孟祥讀書學古,結茅為屋,不事華侈,其古者與?今又濟之以雪,豈亦表其高潔之志行也歟?寧獨是邪?孟祥之匿于深山而不為世用,窮而在下,如冰雪冱寒之窮冬也;及其以善及人,而有成物之心,其不為果哉者,則又如雪之有生物弭災之功也。以屋名雪,詎不韙歟?至若啟斯屋而觀夫雪之態度,則見于諸作者之形容,予不暇多記也。
水國西風小搖落,撩人羈緒亂如絲。 大夫澤畔行吟處,司馬江頭送別時。 爾輩何傷吾道在,此心惟有彼蒼知。 蒼顏華發今如許,便掛衣冠已是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