懷明叔三首
結交不在早,傾蓋有馀歡。愧比陳蕃榻,猶吾陋巷簞。
新來幾日別,無計百憂寬。世俗輕交態,相期在歲寒。
紛紛閱投刺,往往盡冠儒。歲晚見松柏,火炎知珷玞。
寒廳憐我獨,玉趾賴君迂。政爾如修竹,何能一日無。
微風吹甚清,缺月照同盈。盤礴得露坐,喧闐嫌市聲。
何勝憶玄度,底處覓彌明。念我筠窗底,蕭然榻正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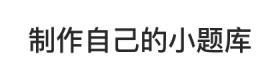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結交不在早,傾蓋有馀歡。愧比陳蕃榻,猶吾陋巷簞。
新來幾日別,無計百憂寬。世俗輕交態,相期在歲寒。
紛紛閱投刺,往往盡冠儒。歲晚見松柏,火炎知珷玞。
寒廳憐我獨,玉趾賴君迂。政爾如修竹,何能一日無。
微風吹甚清,缺月照同盈。盤礴得露坐,喧闐嫌市聲。
何勝憶玄度,底處覓彌明。念我筠窗底,蕭然榻正橫。
結交朋友不在于相識時間早,初次相逢也能有不盡的歡樂。我慚愧比不上陳蕃特設一榻接待徐稚,只能像顏回那樣身處陋巷以簞食瓢飲度日。剛分別才幾天,卻沒有辦法消解這百般憂愁。世俗之人看輕交友之道,我們相約要在艱難時堅守情誼。看那紛紛遞上名帖的人,大多是戴著儒冠的人。到了年末才看出松柏的堅貞,烈火燃燒才能分辨出珷玞與美玉。寒冷的廳堂中可憐我獨自一人,幸虧你屈尊來訪。你就像修長的竹子,我怎么能一天沒有你相伴。微風吹來十分清爽,殘缺的月亮照著我們同樣圓滿的心境。我們隨意地露天而坐,厭煩那喧鬧的街市聲音。我是多么想念你,到哪里去尋覓你這樣的人。想著我在竹窗之下,寂寞地橫躺在榻上。
傾蓋:途中相遇,停車交談,車蓋接近。形容一見如故。
陳蕃榻:陳蕃為豫章太守時,不接待賓客,只為徐稚特設一榻,徐稚走后就把榻掛起來。
陋巷簞:出自《論語》,顏回“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,回也不改其樂”。
投刺:投遞名帖。
珷玞:似玉的美石。
玉趾:對人腳步的敬稱。
迂:繞道,這里指屈尊來訪。
玄度:東晉許詢,字玄度,有才藻。
彌明:唐代衡山道士軒轅彌明。
筠窗:竹窗。
具體創作時間和地點難以確切考證。從詩中可推測,詩人可能處于一種孤獨寂寞的狀態,在與友人分別后,感慨世俗交友的淡薄,從而更加珍惜與友人的情誼,于是創作此詩表達對友人的思念和對真摯友情的堅守。
這首詩主旨是表達對友人的思念和對真摯友情的珍視。突出特點是運用意象和典故,以質樸語言展現深刻情感。在文學上體現了古人對友情的重視和追求。
京洛皇居,芳禊春馀。影媚元巳,和風上除。云開翠帟, 水騖鮮居。林渚縈映,煙霞卷舒。花飄粉蝶,藻躍文魚。 沿波式宴,其樂只且。
南北短長亭,行路無情客有情。年去年來鞍馬上,何成!短鬢垂垂雪幾莖。 孤舍一檠燈,夜夜看書夜夜明。窗外幾竿君子竹,凄清,時作西風散雨聲。
山河縈帶九州橫。深谷幾為陵。千年萬年興廢,花月洛陽城。圖富貴,論功名。我無能。一壺春酒,數首新詩,實訴衷情。
干荷葉,色蒼蒼,老柄風搖蕩,減了清香。越添黃。都因昨夜一場霜,寂寞在秋江上。
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*笠,綠蓑衣。風雨不須歸。管甚做、人間是非。兩肩云衲,一枝筇杖,盡日可忘機。之子欲何為。歸去來、山猿怪遲。
到閑人閑處,更何必,問窮通。但遣興哦詩,洗心觀易,散步攜筇。浮云不堪攀慕,看長空、淡淡沒孤鴻。今古漁樵話里,江山水墨圖中。千年事業一朝空。春夢曉聞鐘。得史筆標名,云臺畫像,多少成功。歸來富春山下,笑狂奴、何事傲三公。塵事休隨夜雨,扁舟好待秋風。
詩酒休驚誤一生。黃塵南北路、幾功名。枝頭烏鵲夢頻驚。西州月,夜夜照人明。枕上數寒更。西風殘漏滴、兩三聲。客中新感故園情。音書斷,天曉雁孤鳴。
秋山落葉秋聲瑟,遠水浮天天一色。 日暮惟見平湖深,扁舟遙界天光碧。 此時南雁正為群,此際悲鳴斷續聞。 幾處凄酸叫涼月,數聲嘹亮破寒云。 云破天清月浸沙,無端哀咽向蘆花。 早梅暗落高樓笛,楊柳驚飛出塞笳。 幽修似伴魚龍語,更共啼烏催窗曙。 思婦天涯夢不成,征人故國淚如雨。 曾說聽猿易斷腸,那知聞雁重悲傷。 九秋霜露寒更苦,千里關山夜獨長。 塞北江南天浩浩,斜飛欲盡衡陽道。 足下何曾寄客書,聲中只解催人老。 人生真憂是別離,他鄉霜月易成悲。 誰家錦幌銀屏夜,過盡寒聲獨未知。
梧桐聲脫秋聲起,迢迢秋色澹如水。 天上佳期玉露中,人閑良夜金波里。 此時漢使向河源,此夕乘槎犯斗垣。 但驚城舍嚴官府,那識天孫遇河鼓。 云階月地難久留,飄然枯木復乘流。 歸來不問成都卜,肯信身親見女牛。 從此人疑有天路,俱言河漢清可度。 帝子英靈空有人,千秋別淚自沾巾。 可憐匹練高樓色,年年愁殺問津人。
綠水紅蕖欲斷腸,可憐秋色似橫塘。 晚風不見木蘭枻,明月無人花自香。
鷓鴣南枝鳥,愁隨北雁去。 儂家是江南,但愛江南住。
一望家山上虎丘,凄然魄動念同游。林巒不改如平日,蒲柳先衰又幾秋。
敢學登臨小東魯,卻因零落恨西州。鸰原寂寞歸鴻斷,未拂前題已淚流。
酒泉城外碧云端,萬疊芙蓉雪未干。素影欲迷銀漢迥,晴光不逐暖風殘。
氣吞沙漠千山遠,勢壓番戎六月寒。公館日長清似水,幾回吟望倚欄桿。
韓文公之文,起八代之衰,其詩亦怪怪奇奇,獨辟門戶,而考亭先生嘗病其俗,曰《上宰相書》、《讀書城南詩》是也。豈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進,志在利祿乎?故吾嘗謂文章之事,未論其他,必先去其俗而后可。今天下多文人矣,身在草莽,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,且朝作一文,暮鐫于梓,往往成巨帙,干謁貴人及結納知名之士,則挾以為贄,如此,文雖佳,俗矣。吾讀嚴子祺先之文,深嘆其能矯然拔俗也。無錫自顧端文、高忠憲兩先生講道東林,遠紹絕學,流風未遠。嚴子生于其鄉,誦遺書,沐馀教,被服儒者,邃于經學。平日重名節,慎行藏,視世之名位利祿,若將浼焉。感憤郁塞,觸事而發,故其文立言之旨,多今人之笑為迂者。韓子嘗言:“人笑之,則心以為喜。”夫人之笑韓子者,特以其文辭為流俗所笑,猶杰然為一代儒宗;若立言之旨為流俗所笑,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!雖然,使韓子而居今之世,其立言之旨,當亦如嚴子之迂,必不至有上宰相之書、城南之詩,取譏于大儒矣。嚴子之文,余所見止數十篇,論理論事,明快嚴峭,恂恂儒者而筆能殺人,文辭之工如此!然吾以為文辭之工,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,亦或能之;其所以矯然拔俗,乃在立言之旨,世所共笑為迂者也。夫世共笑為迂,余獨不以為迂,而欣賞嘆詫,則余亦迂甚矣哉!
德澤波斯淡,謳歌載路聞。偕民登壽域,不老是神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