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和歌辭:三閣詞四首
貴人三閣上,日晏未梳頭。不應有恨事,嬌甚卻成愁。
珠箔曲瓊鉤,子細見揚州。北兵那得度,浪語判悠悠。
沉香帖閣柱,金縷畫門楣。回首降幡下,已見黍離離。
三人出眢井,一身登檻車。朱門漫臨水,不可見鱸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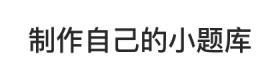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貴人三閣上,日晏未梳頭。不應有恨事,嬌甚卻成愁。
珠箔曲瓊鉤,子細見揚州。北兵那得度,浪語判悠悠。
沉香帖閣柱,金縷畫門楣。回首降幡下,已見黍離離。
三人出眢井,一身登檻車。朱門漫臨水,不可見鱸魚。
尊貴的美人在三閣之上,天色已晚還未梳頭。本不應有什么憾事,卻因太過嬌嗔反而生出愁緒。珍珠簾子用彎曲的玉鉤掛起,仔細看能望見揚州。北方的軍隊怎么能渡過江呢,那些傳言真是毫無根據。沉香木貼在樓閣的柱子上,門楣用金線描繪。回首間看到投降的旗幟降下,已見莊稼長得一片繁茂。三個人從枯井中出來,一人被押上囚車。朱門空自臨著江水,卻再也看不到鱸魚。
貴人:指陳后主的寵妃張麗華等。日晏:天色晚。珠箔:珍珠簾子。曲瓊鉤:彎曲的玉鉤。子細:仔細。浪語:毫無根據的話。判:斷定。悠悠:形容沒有根據。沉香:一種香木。帖:同“貼”。黍離離:出自《詩經·王風·黍離》,指國家破敗,長滿莊稼。眢井:枯井。檻車:囚車。朱門:紅漆大門,指富貴人家。鱸魚:典出張翰見秋風起而思故鄉鱸魚膾,這里暗指亡國后失去自由。
此詩創作于唐代,以陳朝亡國為背景。陳后主陳叔寶生活奢侈,不理朝政,在光昭殿前起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,與寵妃張麗華等居住其中,日夜游樂。后來隋軍南下,陳朝滅亡。詩人通過這組詩借古諷今,警示當時統治者不要重蹈陳后主覆轍。
這組詩主旨是借陳朝亡國之事,批判統治者的荒淫誤國。其特點是通過鮮明對比展現興衰,用典巧妙。在文學史上,這類詠史詩為后世提供了借鑒,以歷史教訓反映社會現實。
鐵笛穿花去。問長安、市上生涯,而今何似。破帽青衫塵滿面。不識何人共語。且面壁、聽風雨。惟我虛中元識破,笑人間、日月無停杼。名與利,莫輕許。人生窮達皆天鑄。試燈前、為問靈龜,勸君休怒。心肯命通元有數,何幸知音記取。季主也、應留得住。百歲光陰彈指過,算伯夷、盜跖俱塵土。心一寸,人千古。
琴彈十八拍,聽此雙淚流。 一死固已難,萬言復誰尤。 九原見衛子,何語可以酬。
奇芬煦寒洌,龍蛇墨池蜿。頗思日夕從,所惜歲華晚。
頓深循陔心,月杪欲云返。氣聯別愈難,情親景彌短。
相期各千秋,攜手話梅巘。獰飆雖切肌,但覺春意滿。
愛君若皓月,見影即搴幰。明年二月期,屈指未愁遠。
我兄善擇友,半多嵇阮交。見子所為文,久思結同袍。
今直泛鴛水,居然叩蓬蒿。精采固奕奕,詞源更滔滔。
款留宿南園,對壘詩城高。閒騎出挑戰,苦無赫連刀。
緩兵得奇計,一醉方陶陶。
太原裼裘來,群知是天人。阿瞞捉刀立,胡奴諦其真。
濁世尚皮毛,抵掌效儀秦。毋乃優孟似,不足對大賓。
鸞皇半空翔,肯與鵝鶩馴?輪囷復芬郁,我方識卿云。
讀君詩百回,一讀輒膽落。洪壚烈焰騰,霜雪忽回薄。
豹隱極窅窱,鵬搏振寥廓。龍文百斛扛,太華千仞削。
不意麋鹿姿,乃邀騏驥托。聯吟怯郊寒,且赴城南約。
娉娉裊裊十三余,豆蔻梢頭二月初。 春風十里揚州路,卷上珠簾總不如。
多情卻似總無情,唯覺尊前笑不成。(尊 一作:樽) 蠟燭有心還惜別,替人垂淚到天明。
茲地五湖鄰,艱哉萬里人。驚飆翻是托,危浪亦相因。 宣室才華子,金閨諷議臣。承明有三入,去去速歸輪。
至陽之精,內含文明。成命宥密,神化陰騭。倬元圣而緯天,爍靈符之在日。人文變見,元象貞吉。煥爾殊容,昭然異質。三陽并列,契干體以成三;一氣貫中,表圣人之得一。當是時也,河清海晏,時和歲豐。車書混合,華夷會同。皇帝乃率百吏,禋六宗。登臺視朔,候律占風。祀夕月于禮神之館,拜朝日于祈年之宮。霽氛霧,掃煙虹。地涯靜,天宇空。陰魄既沒,大明在東。吐象成字,昭文有融。法科斗以為體,并踆烏以處中。馮相未覿,疇人發蒙。此乃圣人合契,至化元通。不然者,何得曜靈起瑞,明被于有截;垂光燭地,運行而無窮?圣人以不宰成能,日月以無私可久。偶圣則呈祥,逢昏則顯咎。貞觀契無為之功,休祥應無疆之壽。沒于地,我則取誡于明夷;登于天,我則呈形于大有。其初見也,昭昭彰彰,流晶耀芒。若神龍負圖兮,呈八卦于羲皇。其少登也,發色騰光,乍見乍藏。狀靈龜銜書兮,錫九疇于夏王。蔽虧若木,隱映扶桑。曈昽五云之表,輝映重輪之旁。
宿云如墨繞湖堤,黃柳青蒲咫尺迷。 行到畫橋天忽醒,誰家茅屋一聲雞。
蠟痕初染仙莖露,新聲又移涼影。佩玉流空,綃衣翦霧,幾度槐昏柳暝。幽窗睡醒。奈欲斷還連,不堪重聽。怨結齊姬,故宮煙樹翠陰冷。 當時舊情在否,晚妝清鏡里,猶記嬌鬢。亂咽頻驚,余悲漸杳,搖曳風枝未定。秋期話盡。又抱葉凄凄,暮寒山靜。付與孤蛩。苦吟清夜永。
羿請無死之藥于西王母,嫦娥竊之以奔月,將往,枚筮之于有黃。有黃占之曰:“吉。翩翩歸妹,獨將西行。逢天晦芒,毋恐毋驚。后且大昌。”嫦娥遂托身于月,是為“蟾蠩”。
舊說太古之時,有大人遠征,家無余人,唯有一女。牡馬一匹,女親養之。窮居幽處,思念其父,乃戲馬曰:“爾能為我迎得父還,吾將嫁汝。”馬既承此言,乃絕韁而去。徑至父所。父見馬,驚喜,因取而乘之。馬望所自來,悲鳴不已。父曰:“此馬無事如此,我家得無有故乎?”亟乘以歸。
為畜生有非常之情,故厚加芻養。馬不肯食。每見女出入,輒喜怒奮擊。如此非一。父怪之,密以問女,女具以告父:“必為是故。”父曰:“勿言。恐辱家門。且莫出入。”于是伏弩射殺之。暴皮于庭。
父行,女以鄰女于皮所戲,以足蹙之曰:“汝是畜生,而欲取人為婦耶!招此屠剝,如何自苦!”言未及竟,馬皮蹶然而起,卷女以行。鄰女忙怕,不敢救之。走告其父。父還求索,已出失之。
后經數日,得于大樹枝間,女及馬皮,盡化為蠶,而績于樹上。其(上爾下蟲)綸理厚大,異于常蠶。鄰婦取而養之。其收數倍。因名其樹曰桑。桑者,喪也。由斯百姓競種之,今世所養是也。《搜神記》
豫章新喻縣男子,見田中有六七女,皆衣毛衣,不知是鳥。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,取藏之,即往就諸鳥。諸鳥各飛去,一鳥獨不得去。男子取以為婦。生三女。其母后使女問父,知衣在積稻下,得之,衣而飛去,后復以迎三女,女亦得飛去。《搜神記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