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范信中寓居崇寧遇雨二首 其一
范侯來尋八桂路,走避俗人如脫兔。
衣囊夜雨寄禪家,行潦升階漂兩屨。
遣悶悶不離眼前,避愁愁已知人處。
慶公憂民苗未立,旻公憂木水推去。
兩禪有意開壽域,歲晚筑室當百堵。
他時無屋可藏身,且作五里公超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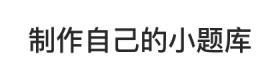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范侯來尋八桂路,走避俗人如脫兔。
衣囊夜雨寄禪家,行潦升階漂兩屨。
遣悶悶不離眼前,避愁愁已知人處。
慶公憂民苗未立,旻公憂木水推去。
兩禪有意開壽域,歲晚筑室當百堵。
他時無屋可藏身,且作五里公超霧。
范侯前來尋找前往八桂的道路,躲避世俗之人如同脫逃的兔子般敏捷。衣囊在夜雨里寄放在寺院,路上積水漫上臺階,打濕了兩雙鞋子。排遣煩悶卻發現煩悶仍在眼前,躲避愁緒而愁緒早已知曉人的去處。慶公擔憂百姓的禾苗尚未立穩,旻公擔憂樹木被雨水沖去。兩位僧人有意為眾人開辟安養之地,年末將筑起百堵房屋。將來若無處可藏身,暫且化作五里公超霧避世。
八桂路:代指廣西一帶,八桂為廣西雅稱。
脫兔:出自《孫子兵法》“動如脫兔”,形容動作迅速。
禪家:指寺院。
行潦(lǎo):路上的積水。
屨(jù):鞋子。
壽域:原指長壽之境,此處指安身聚居之地。
百堵:形容房屋眾多,堵為墻的計量單位。
公超霧:用典,指東漢張楷(字公超)隱居時能作五里霧,代指避世手段。
此詩或為作者與友人范信中寓居崇寧(今屬廣西)時遇雨所作。崇寧地處僻遠,二人避世途中遇雨,暫居寺院,目睹雨水對民生(禾苗、樹木)的影響,又感于兩位僧人的善舉,遂作此詩唱和,記錄當下境遇與內心感慨。
全詩以遇雨寄禪的經歷為線索,既描繪避世途中的現實困頓(夜雨濕屨、愁悶難遣),又展現對安身之所的期待(僧人筑室)與避世決心(化作公超霧),融合生活細節與理想追求,體現詩人對避世生活的復雜體悟。
人在年少,神情未定,所與款狎,熏漬陶染,言笑舉動,無心于學,潛移暗化,自然似之。何況操履藝能,較明易習者也?是以與善人居,如入芝蘭之室,久而自芳也;與惡人居,如入鮑魚之肆,久而自臭也。《顏氏家訓》
古之學者為己,以補不足也;今之學者為人,但能說之也。古之學者為人,行道以利世也;今之學者為己,修身以求進也。夫學者猶種樹也,春玩其華,秋登其實;講論文章,春華也,修身利行,秋實也。《顏氏家訓》
學之所知,施無不達。世人讀書者,但能言之,不能行之,忠孝無聞,仁義不足;加以斷一條訟,不必得其理;宰千戶縣,不必理其民;問其造屋,不必知楣橫而悅豎也;問其為田,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;吟嘯談謔,諷詠辭賦,事既優閑,材增迂誕,軍國經綸,略無施用;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,良由是乎?
夫學者所以求益耳。見人讀數十卷書,便自高大,凌忽長者,輕慢同列;人疾之如仇敵,惡之如鴟梟。如此以學自損,不如無學也。
古之學者為己,以補不足也;今之學者為人,但能說之也。古之學者為人,行道以利世也;今之學者為己,修身以求進也。夫學者猶種樹也,春玩其華,秋登其實;講論文章,春華也,修身利行,秋實也。
齊朝有一士大夫,嘗謂吾曰:“我有一兒,年已十七,頗曉書疏。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,以此伏事公卿,無不寵愛,亦要事也。”吾時睥倪而不答。異哉,此人之教子也!若由此業,自致卿相,亦不愿汝曹為之。
邂逅溪源一夢中,空余羅袖疊春叢。 生憐煙杏勻肌薄,不分江梅映肉紅。 要識臨塘比西子,便須索酒對東風。 隨君拄杖敲門去,莫惜觥船一棹空。
曉鶯聲里。睡思酣猶美。旖旎紅娘冰雪體。洛女巫娥浮靡。紫騮踏月嘶風。華裾織翠青蔥。歸去一場春夢,空吟舊綠新紅。
分得藩符近海濱,溪山清處養天真。 幅巾隱幾春菴靜,直是義皇已上人。
倉卒蠻鼙上水濱,使君忠憤獨亡身。 平明戈劍摧城闔,俄頃衣冠落路塵。 志士一門能許國,老夫當日亦知人。 朝廷贈禭哀榮極,青骨千金合有神。
人生七十,都道是、自古世間稀有。今日華堂,阿彌初度,更綿綿增壽。花柳呈妍香云靄,正好暮春時候。江山如畫,百年風景依舊。最喜蘭玉森森,彩衣齊拜,舞塤*迭奏。羅綺香中蟠桃熟,爭獻瑤池王母。愧忝姻聯倚莊椿,瓊樹歲寒長久。歌詞一闋,敬稱千歲春酒。
巢父者,堯時隱人也。山居不營世利,年老以樹為巢,而寢其上,故時人號曰巢父。堯之讓許由也,由以告巢父,巢父曰:“汝何不隱汝形,藏汝光,若非吾友也!”擊其膺而下之,由悵然不自得。乃過清泠之水,洗其耳,拭其目,曰:“向聞貪言,負吾之友矣!”遂去,終身不相見。
許由,字武仲,堯聞致天下而讓焉,乃退而遁于中岳穎水之陽,箕山之下隱。堯又召為九州長,由不欲聞之,洗耳于穎水濱。時有巢父牽牛欲飲之,見由洗耳,問其故。對曰:“堯欲召我為九州長,惡聞其聲,是故洗耳。”巢父曰:“子若處高岸深谷,人道不通,誰能見子?子故浮游,欲聞求其名譽,污我犢口!”牽牛上流飲之。《高士傳》
夏馥字子治,陳留圉人也。少為諸生,質直不茍,動必依道。同縣高儉及蔡氏,凡二家豪富,郡人畏事之,唯馥閉門不與高、蔡通。桓帝即位,災異數發,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。太尉趙戒舉馥,不詣,遂隱身久之。靈帝即位,中常侍曹節等專朝,禁錮善士,謂之黨人。馥雖不交時官,然聲名為節等所憚,遂與汝南范滂、山陽張儉等數百人并為節所誣,悉在黨中。詔下郡縣,各捕以為黨魁。馥乃頓足而嘆曰:“孽自已作,空污良善。一人逃死,禍及萬家,何以生為?”乃自翦須,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,為冶工客作,形貌毀悴,積傭三年,而無知者。后詔委放,儉等皆出,馥獨嘆曰:“已為人所棄,不宜復齒鄉里矣!”留賃作不歸,家人求不知處。其后,人有識其聲者,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,使人以車迎馥,馥自匿不肯,潛車三返,乃得馥。
蓋詩有六義焉,其二曰賦。楊雄曰:“詩人之賦麗以則。”班固曰:“賦者,古詩之流也。”先王采焉,以觀土風。見“綠竹猗猗”,則知衛地淇澳之產;見“在其版屋”,則知秦野西戎之宅。故能居然而辨八方。
然相如賦上林而引“盧橘夏熟”;楊雄賦甘泉而陳“玉樹青蔥”,班固賦西都,而嘆以出比目;張衡賦西京,而述以游海若。假稱珍怪,以為潤色,若斯之類,匪啻于茲。考之果木,則生非其壤;校之神物,則出非其所。于辭則易為藻飾,于義則虛而無征。且夫玉卮無當,雖寶非用;侈言無驗,雖麗非經。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,作者大氐舉為憲章。積習生常,有自來矣。
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,其山川城邑,則稽之地圖;其鳥獸草木,則驗之方志;風謠歌舞,各附其俗;魁梧長者,莫非其舊。何則?發言為詩者,詠其所志也;升高能賦者,頌其所見也。美物者,貴依其本;贊事者,宜本其實。匪本匪實,覽者奚信?且夫任土作貢,虞書所著;辯物居方,周易所慎。聊舉其一隅,攝其體統,歸諸詁訓焉。
九峰南望碧嵯峨,汶水平添一丈波。 渡口客來休更過,北溪山雨正滂沱。
星軺夜落錦江邊,萬里來依刺史天。 才了銓衡三考績,便勤督府一金筵。 綠尊敬酢青田酒,翠袖爭扶紫橐仙。 飲罷嘉定歸底處,三槐陰里望貂蟬。
舒卷意何窮,縈流復帶空。 有形不累物,無跡去隨風。 莫怪長相逐,飄然與我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