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公再和亦再答之
寒雞知將晨,饑鶴知夜半。
亦如老病客,遇節嘗感嘆。
光陰等敲石,過眼不容玩。
親友如摶沙,放手還復散。
羈孤每自笑,寂寞誰肯伴。
元達號神君,高論森月旦。
紀明本賢將,汩沒事堆案。
欣然肯相顧,夜閣燈火亂。
盤空愧不飽,酒薄僅堪盥。
雍容許著帽,不怪安石緩。
雖無窈窕人,清唱弄珠貫。
幸有縱橫舌,說劍起慵懦。
二豪沉下位,暗火埋濕炭。
豈似草玄人,默默老儒館。
行看富貴逼,炙手借余暖。
應念苦思歸,登樓賦王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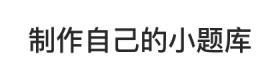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寒雞知將晨,饑鶴知夜半。
亦如老病客,遇節嘗感嘆。
光陰等敲石,過眼不容玩。
親友如摶沙,放手還復散。
羈孤每自笑,寂寞誰肯伴。
元達號神君,高論森月旦。
紀明本賢將,汩沒事堆案。
欣然肯相顧,夜閣燈火亂。
盤空愧不飽,酒薄僅堪盥。
雍容許著帽,不怪安石緩。
雖無窈窕人,清唱弄珠貫。
幸有縱橫舌,說劍起慵懦。
二豪沉下位,暗火埋濕炭。
豈似草玄人,默默老儒館。
行看富貴逼,炙手借余暖。
應念苦思歸,登樓賦王粲。
寒雞知曉即將破曉,饑鶴感知夜半時分。就像年老多病的旅人,逢節令總生感嘆。光陰如同敲擊石火,轉瞬即逝不容把玩。親友如同手中握沙,松開手便復又離散。漂泊孤苦常自嘲笑,寂寞之中誰愿相伴。元達素有神君之稱,高談闊論如評月旦。紀明本是賢能將領,卻埋沒于公文堆案。幸得二位欣然來訪,夜閣中燈火紛亂。盤中空乏難飽客腹,酒液淡薄僅可盥手。雍容大度容許戴帽,不責怪我如安石遲緩。雖無嬌美歌女相伴,但清越歌聲如珠玉連貫。幸有善辯的縱橫之舌,談劍激發慵懶懦弱。二位豪杰沉于下僚,如暗火埋在濕炭之中。怎像我這作《太玄》的揚雄,默默老死在儒學館中。眼看富貴即將逼近,或可借余溫炙手。應念我苦苦思歸,如王粲作《登樓賦》般傷懷。
摶沙:握沙,比喻難以久留。
月旦:指品評人物,源自《后漢書·許劭傳》中許劭、許靖每月初一評論鄉黨人物。
汩沒(gǔ mò):埋沒。
盥(guàn):洗手。
安石:指東晉謝安,此處借指從容的態度。
弄珠貫:形容歌聲如連貫的珠玉。
縱橫舌:指能言善辯的口才。
草玄人:指揚雄,其作《太玄經》,后借指潛心著述之人。
炙手:比喻權勢極盛,如成語“炙手可熱”。
登樓賦王粲:王粲《登樓賦》為思鄉名篇,此處借指思歸之情。
此詩為蘇軾與友人唱和之作。具體創作時間或在其任職或貶謫期間,詩中“元達”“紀明”當為當時友人。蘇軾一生宦海沉浮,與友朋多有唱和,此詩或作于其處境較為困頓之時,故詩中多有對時光、親友及自身際遇的感慨。
全詩以日常場景與典故交織,圍繞時光流逝、親友離散、與友相會展開,既抒個人漂泊之嘆,又寄對友人懷才不遇的同情,最終以思歸作結。語言質樸,情感真摯,展現了蘇軾對人生際遇的深刻思考。
春漠漠,雨絲絲。杏花低亞小樓時。倚闌脈脈閒凝睇,春在梢頭總未知。
尺幅誰圖寫,塊礧寄其胸。超然與物,無忤綽有阮嵇風。
詎識渭濱嚴瀨,多少文經武緯,只在卷舒中。暫爾謝塵網,分付白云封。
一溪水,千丈壁,萬株松。煙波浩渺,收拾釣艇與詩筒。
莫問蟻王鹿逐,但看鳥婚花嫁,變態亦何窮。放眼乾坤大,海闊復天空。
離離一樹海棠花,是誰栽墻角?到而今、孤館鎖寒煙,只有東風吹著。
紅英糝地殘香薄。似馬嵬漂泊。縱饒此際,春閨睡足,也應傷寥落。
鈴閣雨,寺樓鐘。迸入零香碎玉中。幽夢忽驚啼鳥喚,賣花聲過小樓東。
能白更兼黃,無人亦自芳。 寸心原不大,容得許多香。
蔓草荒煙,問誰氏、斷碑磨滅。爭道是、向家幼女,持貞矢節。
待字年時身未嫁,于歸欲賦夫先沒。卻等閒、不說未亡人,心如鐵。
私恩少,情偏切。大義凜,志尤決。盡滿腔孤憤,刀痕迸裂。
地下青燐應烈焰,閨中紅粉成英杰。只年年、寒食杜鵑啼,流紅血。
秋水蒹葭,夕陽禾黍,一行雁字青天寫。望來北陌南阡,紫粒紅芒,低垂穎粟迎風亞。
白云堆里晚花香,黃茅屋外鐮刀掛。?稏。驀地鸕鶿飛下。
畦邊唼呷呼兒打。不道天與豐盈,物宜咸若,何惜區區者。
不如酤酒樂西成,好齊物我忘虞詐。
雨漣漣,煙冥冥。煙雨連朝,白晝渾如暝。天外云嵐簾外影。
老眼昏花,書籍猶堪枕。
悶無端,愁欲寢。燕子喃喃,忽的驚人醒。王謝家兒難記省。
舉目山河,已自殊風景。
江岸曉霜飄。襆被裝成上小舠。自笑今年空浪跡,如皋。
風雪歸來冷布袍。
回首也蕭騷。十丈愁城無計消。差喜擔頭馀長物,椰瓢。
博得童兒笑語高。
江東歲歲花稠密。盡染啼鵑血。如何幻出水云黃。可是學來仙子道家妝。
美人甘自埋塵土。羞與紅顏伍。英雄事業已沈淪。只有黃沙滾滾楚江濱。
流水繞頹垣。乂手遙憐。有人放鶴暮云邊。讀罷黃庭明月上,松韻翛然。
此景共誰言?古樹寒煙。龐眉不記種桃年。但說主人歸去也,鳥雀喧闐。
懶云窩,醒時詩酒醉時歌。瑤琴不理拋書臥,無夢南柯。得清閑盡快活,日月似攛梭過,富貴比花開落。青春去也,不樂如何?
懶云窩,醒時詩酒醉時歌。瑤琴不理拋書臥,盡自磨陀。想人生待則么?富貴比花開落,日月似攛梭過。呵呵笑我,我笑呵呵。
懶云窩,客至待如何?懶云窩里和衣臥,盡自婆娑。想人生待則么?貴比我高些個,富比我松些個?呵呵笑我,我笑呵呵。
康熙五十一年三月,余在刑部獄,見死而由竇出者,日四三人。有洪洞令杜君者,作而言曰:“此疫作也。今天時順正,死者尚稀,往歲多至日數十人。”余叩所以。杜君曰:“是疾易傳染,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。而獄中為老監者四,監五室,禁卒居中央,牖其前以通明,屋極有窗以達氣。旁四室則無之,而系囚常二百余。每薄暮下管鍵,矢溺皆閉其中,與飲食之氣相薄,又隆冬,貧者席地而臥,春氣動,鮮不疫矣。獄中成法,質明啟鑰,方夜中,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,無可旋避,此所以染者眾也。又可怪者,大盜積賊,殺人重囚,氣杰旺,染此者十不一二,或隨有瘳,其駢死,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。”余曰:“京師有京兆獄,有五城御史司坊,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?”杜君曰:“邇年獄訟,情稍重,京兆、五城即不敢專決;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,皆歸刑部;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、獄官、禁卒,皆利系者之多,少有連,必多方鉤致。茍入獄,不問罪之有無,必械手足,置老監,俾困苦不可忍,然后導以取保,出居于外,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,而官與吏剖分焉。中家以上,皆竭資取保;其次‘求脫械居監外板屋,費亦數十金;惟極貧無依,則械系不稍寬,為標準以警其余。或同系,情罪重者,反出在外,而輕者、無罪者罹其毒。積憂憤,寢食違節,及病,又無醫藥,故往往至死。”余伏見圣上好生之德,同于往圣。每質獄詞,必于死中求其生,而無辜者乃至此。儻仁人君子為上昌言: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,其輕系及牽連未結正者,別置一所以羈之,手足毋械。所全活可數計哉?或曰:“獄舊有室五,名曰現監,訟而未結正者居之。儻舉舊典,可小補也。杜君曰:“上推恩,凡職官居板屋。今貧者轉系老監,而大盜有居板屋者。此中可細詰哉!不若別置一所,為拔本塞源之道也。”余同系朱翁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,遘疫死,皆不應重罰。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,左右鄰械系入老監,號呼達旦。余感焉,以杜君言泛訊之,眾言同,于是乎書。
凡死刑獄上,行刑者先俟于門外,使其黨入索財物,名曰“斯羅”。富者就其戚屬,貧則面語之。其極刑,曰:“順我,即先刺心;否則,四肢解盡,心猶不死。”其絞縊,曰:“順我,始縊即氣絕;否則,三縊加別械,然后得死。”唯大辟無可要,然猶質其首。用此,富者賂數十百金,貧亦罄衣裝;絕無有者,則治之如所言。主縛者亦然,不如所欲,縛時即先折筋骨。每歲大決,勾者十四三,留者十六七,皆縛至西市待命。其傷于縛者,即幸留,病數月乃瘳,或竟成痼疾。余嘗就老胥而問焉:“彼于刑者、縛者,非相仇也,期有得耳;果無有,終亦稍寬之,非仁術乎?”曰:“是立法以警其余,且懲后也;不如此,則人有幸心。”主梏撲者亦然。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:一人予三十金,骨微傷,病間月;一人倍之,傷膚,兼旬愈;一人六倍,即夕行步如平常。或叩之曰:“罪人有無不均,既各有得,何必更以多寡為差?”曰:“無差,誰為多與者?”孟子曰:“術不可不慎。”信夫!
部中老胥,家藏偽章,文書下行直省,多潛易之,增減要語,奉行者莫辨也。其上聞及移關諸部,猶未敢然。功令: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,止主謀一二人立決;余經秋審皆減等發配。獄詞上,中有立決者,行刑人先俟于門外。命下,遂縛以出,不羈晷刻。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,法應立決,獄具矣,胥某謂曰:“予我千金,吾生若。”叩其術,曰:“是無難,別具本章,獄詞無易,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,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。”其同事者曰:“是可欺死者,而不能欺主讞者,倘復請之,吾輩無生理矣。”胥某笑曰:“復請之,吾輩無生理,而主讞者亦各罷去。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,則吾輩終無死道也。”竟行之,案末二人立決。主者口呿舌撟,終不敢詰。余在獄,猶見某姓,獄中人群指曰:“是以某某易其首者。”胥某一夕暴卒,眾皆以為冥謫云。
凡殺人,獄詞無謀、故者,經秋審入矜疑,即免死。吏因以巧法。有郭四者,凡四殺人,復以矜疑減等,隨遇赦。將出,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。或叩以往事,一一詳述之,意色揚揚,若自矜詡。噫!渫惡吏忍于鬻獄,無責也;而道之不明,良吏亦多以脫人于死為功,而不求其情,其枉民也亦甚矣哉!
奸民久于獄,與胥卒表里,頗有奇羨。山陰李姓以殺人系獄,每歲致數百金。康熙四十八年,以赦出。居數月,漠然無所事。其鄉人有殺人者,因代承之。蓋以律非故殺,必久系,終無死法也。五十一年,復援赦減等謫戍,嘆曰:“吾不得復入此矣!”故例: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。時方冬停遣,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,至再三,不得所請,悵然而出。
先君子嘗言,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,一日,風雪嚴寒,從數騎出,微行入古寺,廡下一生伏案臥,文方成草;公閱畢,即解貂覆生,為掩戶。叩之寺僧,則史公可法也。及試,吏呼名至史公,公瞿然注視,呈卷,即面署第一。召入,使拜夫人,曰:“吾諸兒碌碌,他日繼吾志者,惟此生耳。”及左公下廠獄,史朝夕獄門外;逆閹防伺甚嚴,雖家仆不得近。久之,聞左公被炮烙,旦夕且死;持五十金,涕泣謀于禁卒,卒感焉。一日,使史更敝衣草屨,背筐,手長镵,為除不潔者,引入,微指左公處。則席地倚墻而坐,面額焦爛不可辨,左膝以下,筋骨盡脫矣。史前跪,抱公膝而嗚咽。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,乃奮臂以指撥眥;目光如炬,怒曰:“庸奴,此何地也?而汝來前!國家之事,糜爛至此。老夫已矣,汝復輕身而昧大義,天下事誰可支拄者!不速去,無俟奸人構陷,吾今即撲殺汝!”因摸地上刑械,作投擊勢。史噤不敢發聲,趨而出。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,曰:“吾師肺肝,皆鐵石所鑄造也!”
崇禎末,流賊張獻忠出沒蘄、黃、潛、桐間。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御。每有警,輒數月不就寢,使壯士更休,而自坐幄幕外。擇健卒十人,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,漏鼓移,則番代。每寒夜起立,振衣裳,甲上冰霜迸落,鏗然有聲。或勸以少休,公曰:“吾上恐負朝廷,下恐愧吾師也。”
史公治兵,往來桐城,必躬造左公第,候太公、太母起居,拜夫人于堂上。
余宗老涂山,左公甥也,與先君子善,謂獄中語,乃親得之于史公云。
孫奇逢,字啟泰,號鐘元,北直容城人也。少倜儻,好奇節,而內行篤修;負經世之略,常欲赫然著功烈,而不可強以仕。年十七,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試。先是,高攀龍、顧憲成講學東林,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。及天啟初,逆奄魏忠賢得政,叨穢者爭出其門,而目東林諸君子為黨。由是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順昌、繆昌期次第死廠獄,禍及親黨。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、張果中傾身為之,諸公卒賴以歸骨,世所傳“范陽三烈士”也。
方是時,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、遼,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。奇逢密上書承宗,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。忠賢大懼,繞御床而泣,以嚴旨遏承宗于中途。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。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征,不起,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,使元儀先之,奇逢亦不應也。其后畿內盜賊數駭,容城危困,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,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,奇逢為教條部署守御,而弦歌不輟。
入國朝,以國子祭酒征,有司敦趣,卒固辭。移居新安,既而渡河,止蘇門百泉。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,逆率子弟躬耕,四方來學,愿留者,亦授田使耕,所居遂成聚。
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,以象山、陽明為宗,及晚年,乃更和通朱子之說。其治身務自刻砥,執親之喪,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。人無賢愚,茍問學,必開以性之所近,使自力于庸行。其與人無町畦,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,必以誠意接之,用此名在天下,而人無忌嫉者。方楊、左在難,眾皆為奇逢危,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,夙重奇逢質行,無不陰為之地者。鼎革后,諸公必欲強起奇逢,平涼胡廷佐曰:“人各有志,彼自樂處隱就閑,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?”居夏峰二十有五年,卒,年九十有二。
河南北學者,歲時奉祀百泉書院,而容城與劉因、楊繼盛同祀,保定與孫文正承宗、鹿忠節善繼并祀學宮,天下無知與不知,皆稱曰夏峰先生。
贊曰:先兄百川聞之夏峰之學者,征君嘗語人曰:“吾始自分與楊、左諸賢同命,及涉亂離,可以犯死者數矣,而終無恙,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。”征君論學之書甚具,其質行,學者譜焉,茲故不論,而獨著其犖犖大者。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,先生力辭不就,眾皆惜之,而少師再用再黜,訖無成功,《易》所謂“介于石,不終日”者,其殆庶幾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