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平樂 木犀
玻璃剪葉。點綴黃金屑。雅淡幽姿風味別。翠影婆娑弄月。秋光占斷江南。清香鼻觀先參。一朵折來和露,烏云髻畔斜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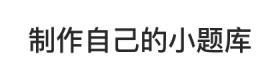
玻璃剪葉。點綴黃金屑。雅淡幽姿風味別。翠影婆娑弄月。秋光占斷江南。清香鼻觀先參。一朵折來和露,烏云髻畔斜簪。
吐握常開北海尊,三吳士女昔沾恩。探驪藝苑傳仙筆,化鶴桑田憶夢痕。
汲古曾稽中壘傳,學詩欲叩魯班門。前人牙慧休重拾,手澤長真十卷存。
誰教玉體兩橫陳,粉黛香消馬上沉。 劉項看來稱敵手,虞夫人后戚夫人。
時為嘉禾小倅,以病眠,不赴府會。
水調數聲持酒聽,午醉醒來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幾時回?臨晚鏡,傷流景,往事后期空記省。 沙上并禽池上瞑,云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簾幕密遮燈,風不定,人初靜,明日落紅應滿徑。
傳舍官如住寺僧,半年暫住此荒城。 湖邊無處看山色,但愛千家帶雨耕。
楚水入洞庭者三:曰蒸湘,曰資湘,曰沅湘;故有“三湘”之名。洞庭即湘水之尾,故君山曰湘山也。資湘亦名瀟湘,今資江發源武岡上游之夫夷水,土人尚曰瀟溪,其地曰蕭地。見《寶慶府志》。《水經注》不言瀟水,而柳宗元別指永州一水為瀟,遂以蒸湘為瀟湘,而三湘僅存其二矣。予生長三湘,溯洄云水,爰為棹歌三章,以正其失,且寄湖山鄉國之思。
天無風雨不成秋,只當清明上巳游。 楚樹吳云二千里,滿天黃葉獨登樓。
夷陵形勝地,高距楚云中。峽路三巴接,江流九派通。
文章留爾雅,割據失英雄。尚憶平成日,黃牛佐禹功。
五更寒襲紫毛衫,睡起東窗酒尚酣。 門外日高晴不得,滿城濕露似江南。
惲既失爵位家居,治產業,起室宅,以財自娛。歲余,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,知略士也,與惲書,諫戒之。為言大臣廢退,當闔門惶懼,為可憐之意;不當治產業,通賓客,有稱譽。惲宰相子,少顯朝廷,一朝暗昧,語言見廢,內懷不服。報會宗書曰:
惲材朽行穢,文質無所底,幸賴先人余業,得備宿衛。遭遇時變,以獲爵位。終非其任,卒與禍會。足下哀其愚蒙,賜書教督以所不及,殷勤甚厚。然竊恨足下不深推其終始,而猥隨俗之毀譽也。言鄙陋之愚心,若逆指而文過;默而息乎,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。故敢略陳其愚,惟君子察焉。
惲家方隆盛時,乘朱輪者十人,位在列卿,爵為通侯,總領從官,與聞政事。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,以宣德化,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,陪輔朝庭之遺忘,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。懷祿貪勢,不能自退,遂遭變故,橫被口語,身幽北闕,妻子滿獄。當此之時,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,豈意得全首領,復奉先人之丘墓乎?伏惟圣主之恩不可勝量。君子游道,樂以忘憂;小人全軀,說以忘罪。竊自念過已大矣,行已虧矣,長為農夫以末世矣。是故身率妻子,戮力耕桑,灌園治產,以給公上,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。
夫人情所不能止者,圣人弗禁。故君父至尊親,送其終也,有時而既。臣之得罪,已三年矣。田家作苦。歲時伏臘,烹羊炰羔,斗酒自勞。家本秦也,能為秦聲。婦趙女也,雅善鼓瑟。奴婢歌者數人,酒后耳熱,仰天撫缶而呼烏烏。其詩曰:“田彼南山,蕪穢不治。種一頃豆,落而為萁。人生行樂耳,須富貴何時!”是日也,奮袖低昂,頓足起舞;誠滛荒無度,不知其不可也。惲幸有余祿,方糴賤販貴,逐什一之利。此賈豎之事,污辱之處,惲親行之。下流之人,眾毀所歸,不寒而栗。雖雅知惲者,猶隨風而靡,尚何稱譽之有?董生不云乎:“明明求仁義,常恐不能化民者,卿大夫之意也。明明求財利,常恐困乏者,庶人之事也。”故道不同,不相為謀,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仆哉!
夫西河魏土,文侯所興,有段干木、田子方之遺風,凜然皆有節概,知去就之分。頃者足下離舊土,臨安定,安定山谷之間,昆戎舊壤,子弟貪鄙,豈習俗之移人哉?于今乃睹子之志矣!方當盛漢之隆,愿勉旃,毋多談。
子卿足下:
勤宣令德,策名清時,榮問休暢,幸甚幸甚。遠托異國,昔人所悲,望風懷想,能不依依?昔者不遺,遠辱還答,慰誨勤勤,有逾骨肉,陵雖不敏,能不慨然?
自從初降,以至今日,身之窮困,獨坐愁苦。終日無睹,但見異類。韋韝毳幕,以御風雨;羶肉酪漿,以充饑渴。舉目言笑,誰與為歡?胡地玄冰,邊土慘裂,但聞悲風蕭條之聲。涼秋九月,塞外草衰。夜不能寐,側耳遠聽,胡笳互動,牧馬悲鳴,吟嘯成群,邊聲四起。晨坐聽之,不覺淚下。嗟乎子卿,陵獨何心,能不悲哉!
與子別后,益復無聊,上念老母,臨年被戮;妻子無辜,并為鯨鯢;身負國恩,為世所悲。子歸受榮,我留受辱,命也如何?身出禮義之鄉,而入無知之俗;違棄君親之恩,長為蠻夷之域,傷已!令先君之嗣,更成戎狄之族,又自悲矣。功大罪小,不蒙明察,孤負陵心區區之意。每一念至,忽然忘生。陵不難刺心以自明,刎頸以見志,顧國家于我已矣,殺身無益,適足增羞,故每攘臂忍辱,轍復茍活。左右之人,見陵如此,以為不入耳之歡,來相勸勉。異方之樂,只令人悲,增忉怛耳。
嗟乎子卿,人之相知,貴相知心,前書倉卒,未盡所懷,故復略而言之。
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,出征絕域。五將失道,陵獨遇戰,而裹萬里之糧,帥徒步之師;出天漢之外,入強胡之域;以五千之眾,對十萬之軍;策疲乏之兵,當新羈之馬。然猶斬將搴旗,追奔逐北,滅跡掃塵,斬其梟帥,使三軍之士,視死如歸。陵也不才,希當大任,意謂此時,功難堪矣。匈奴既敗,舉國興師。更練精兵,強逾十萬。單于臨陣,親自合圍。客主之形,既不相如;步馬之勢,又甚懸絕。疲兵再戰,一以當千,然猶扶乘創痛,決命爭首。死傷積野,余不滿百,而皆扶病,不任干戈,然陵振臂一呼,創病皆起,舉刃指虜,胡馬奔走。兵盡矢窮,人無尺鐵,猶復徒首奮呼,爭為先登。當此時也,天地為陵震怒,戰士為陵飲血。單于謂陵不可復得,便欲引還,而賊臣教之,遂使復戰,故陵不免耳。
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,困于平城。當此之時,猛將如云,謀臣如雨,然猶七日不食,僅乃得免。況當陵者,豈易為力哉?而執事者云云,茍怨陵以不死。然陵不死,罪也;子卿視陵,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?寧有背君親,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?然陵不死,有所為也,故欲如前書之言,報恩于國主耳,誠以虛死不如立節,滅名不如報德也。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,曹沬不死三敗之辱,卒復勾踐之仇,報魯國之羞,區區之心,竊慕此耳。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,計未從而骨肉受刑,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。
足下又云:“漢與功臣不薄。”子為漢臣,安得不云爾乎?昔蕭樊囚縶,韓彭葅醢,晁錯受戮,周魏見辜。其余佐命立功之士,賈誼亞夫之徒,皆信命世之才,抱將相之具,而受小人之讒,并受禍敗之辱,卒使懷才受謗,能不得展。彼二子之遐舉,誰不為之痛心哉?陵先將軍,功略蓋天地,義勇冠三軍,徒失貴臣之意,剄身絕域之表。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。何謂不薄哉?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,適萬乘之虜。遭時不遇,至于伏劍不顧;流離辛苦,幾死朔北之野。丁年奉使,皓首而歸;老母終堂,生妻去帷。此天下所希聞,古今所未有也。蠻貊之人,尚猶嘉子之節,況為天下之主乎?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,受千乘之賞。聞子之歸,賜不過二百萬,位不過典屬國,無尺土之封,加子之勤。而妨功害能之臣,盡為萬戶侯;親戚貪佞之類,悉為廊廟宰。子尚如此,陵復何望哉?且漢厚誅陵以不死,薄賞子以守節,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,此實難矣,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。陵雖孤恩,漢亦負德。昔人有言:“雖忠不烈,視死如歸。”陵誠能安,而主豈復能眷眷乎?男兒生以不成名,死則葬蠻夷中,誰復能屈身稽顙,還向北闕,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?愿足下勿復望陵。
嗟乎子卿,夫復何言?相去萬里,人絕路殊。生為別世之人,死為異域之鬼。長與足下生死辭矣。幸謝故人,勉事圣君。足下胤子無恙,勿以為念。努力自愛,時因北風,復惠德音。李陵頓首。
三月煙花,二分明月,香車陌上如流。變來今日,犀甲帶吳鉤。
何日王師雨洗,長驅入、迅掃貔貅。危城里,天荊地棘,不是等閑愁。
長淮三百里,回頭一笑,夢也休休。幸分飛兩地,翻謝河洲。
自顧此生安寄,問前生,著甚來由。只馀得,青磷碧血,何處十三樓。
大鐵椎,不知何許人。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,與遇宋將軍家。宋,懷慶青華鎮人,工技擊,七省好事者皆來學,人以其雄健,呼宋將軍云。宋弟子高信之,亦懷慶人,多力善射,長子燦七歲,少同學,故嘗與過宋將軍。
時座上有健啖客,貌甚寢,右脅夾大鐵椎,重四五十斤,飲食拱揖不暫去。柄鐵折疊環復,如鎖上練,引之長丈許。與人罕言語,語類楚聲。扣其鄉及姓字,皆不答。
既同寢,夜半,客曰:“吾去矣!”言訖不見。子燦見窗戶皆閉,驚問信之。信之曰:“客初至,不冠不襪,以藍手巾裹頭,足纏白布,大鐵椎外,一物無所持,而腰多白金。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。”子燦寐而醒,客則鼾睡炕上矣。
一日,辭宋將軍曰:“吾始聞汝名,以為豪,然皆不足用。吾去矣!”將軍強留之,乃曰:“吾數擊殺響馬賊,奪其物,故仇我。久居,禍且及汝。今夜半,方期我決斗某所。”宋將軍欣然曰:“吾騎馬挾矢以助戰。”客曰:“止!賊能且眾,吾欲護汝,則不快吾意。”宋將軍故自負,且欲觀客所為,力請客。客不得已,與偕行。將至斗處,送將軍登空堡上,曰:“但觀之,慎弗聲,令賊知也。”
時雞鳴月落,星光照曠野,百步見人。客馳下,吹觱篥數聲。頃之,賊二十余騎四面集,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。一賊提刀突奔客,客大呼揮椎,賊應聲落馬,馬首裂。眾賊環而進,客奮椎左右擊,人馬仆地,殺三十許人。宋將軍屏息觀之,股栗欲墮。忽聞客大呼曰:“吾去矣。”塵滾滾東向馳去。后遂不復至。
魏禧論曰:子房得力士,椎秦皇帝博浪沙中。大鐵椎其人歟?天生異人,必有所用之。予讀陳同甫《中興遺傳》,豪俊、俠烈、魁奇之士,泯泯然不見功名于世者,又何多也!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歟?抑用之自有時歟?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,視其貌當年三十,然大鐵椎今年四十耳。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,甚工楷書也。
萬安縣有賣酒者,以善釀致富。平生不欺人,或遣童婢沽,必問:“汝能飲酒否?”量酌之,曰:“毋盜瓶中酒,受主翁笞也。”或傾跌破瓶缶,輒家取瓶,更注酒,使持以歸。由是遠近稱長者。
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,相對咨嗟。賣酒者問曰:“諸君何為數聚飲相咨嗟也?”聚飲者曰:“吾儕保甲貸乙金,甲逾期不肯償,將訟。訟則破家,事連吾儕,數姓人不得休矣!”賣酒者曰:“幾何數?”曰:“子母四百金。”賣酒者曰:“何憂為?”立出四百金償之,不責券。
客有橐重資于途者,甚雪,不能行。聞賣酒者長者,趨寄宿。雪連日,賣酒者日呼客同博,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啖。客多負,私怏怏曰:“賣酒者乃不長者耶?然吾已負,且大飲啖,酬吾金也。”雪霽,客償博所負,行。賣酒者笑曰:“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?天寒甚,不名博,客將不肯大飲啖。”盡取所償負還之。
術者談五行,決賣酒者宜死。賣酒者將及期,置酒,召所買田舍主畢至,曰:“吾往買若田宅,若中心愿之乎?價毋虧乎?”欲贖者視券,價不足者,追償以金。又召諸子貸者曰:“汝貸金若干,子母若干矣。”能償者捐其息,貧者立券還之,曰:“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!”其坦然如是。其后,賣酒者活更七年。
魏子曰:吾聞賣酒者好博,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,喧爭無家人禮。或問之,曰:“兒輩嬉,否則博他人家,敗吾產矣。”嗟乎!賣酒者匪唯長者,抑亦智士哉!
滾滾長江東逝水,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。青山依舊在,幾度夕陽紅。 白發漁樵江渚上,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談中。
昔者孔子之弟子,有德行,有政事,有言語、文學,其鄙有樊遲,其狂有曾點。孔子之師,有老聃,有郯子,有萇弘、師襄,其故人有原壤,而相知有子桑伯子。仲弓問子桑伯子,而孔子許其為簡,及仲弓疑其太簡,然后以雍言為然。是故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:“夫子之門,何其雜也?”嗚呼!此其所以為孔子歟?
至于孟子乃為之言曰:“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,楊墨之言不息,孔子之道不著,能言距楊墨者,圣人之徒。”當時因以孟子為好辯。雖非其實,而好辯之端,由是啟矣。唐之韓愈,攘斥佛老,學者稱之。下逮有宋,有洛、蜀之黨,有朱、陸之同異。為洛之徒者,以排擊蘇氏為事;為朱之學者,以詆諆陸子為能。吾以為天地之氣化,萬變不窮,則天下之理,亦不可以一端盡。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,自力行而入;子貢之一以貫之,自多學而得。以后世觀之,子貢是,則曾子非矣。然而孔子未嘗區別于其間,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。夫所惡于楊墨者,為其無父無君也;斥佛老者,亦日棄君臣,絕父子,不為昆弟夫婦,以求其清凈寂滅。如其不至于是,而吾獨何為訾謷之?大盜至,肢篋探囊,則荷戈戟以隨之,服吾之服,而誦吾之言,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。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斗,是亦不可以已乎?
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,見有稍異于己者,則眾起而排之,此不足以論人也。人貌之不齊,稍有巨細長短之異,遂斥之以為非人,豈不過戰?北宮黝、孟施舍,其去圣人之勇蓋遠甚,而孟子以為似曾子、似子夏,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, 以為似曾子、似子夏可也。居高以臨下,不至于爭,為其不足與我角也。至于才力之均敵,而惟恐其不能相勝,于是紛壇之辯以生。是故知道者,視天下之歧趨異說,皆未嘗出于吾道之外,故其心恢然有余;夫恢然有余,而于物無所不包,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。